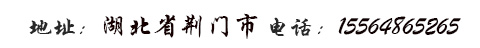王叔武南夷书笺注并考异
|
《南夷书》笺注并考异 王叔武(-),男,安徽桐城市人,云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长期从事云南民族史与地方文献研究。 叙例 《南夷书》一卷,明张洪撰。《明史·艺文志》失载,见于《千顷堂书目·舆地类》,《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存目》著录。洪字宗海,常熟人。洪武中,滴戍云南。永乐元年,任行人司行人,使日本,著有《日本补遗》一书。永乐四年,“缅甸那罗塔杀孟养宣慰刀木旦,并其地。上命洪赍诏,谕缅甸退还侵地。罗塔不服,凡六经往返,始听。罗塔始欲置毒,服其城信,乃已。”归著《南夷书》及《使规》。《使规》“末为《使缅附录》,记当日往返情况,并载所与缅酋书六篇。”天启《滇志》将其事迹列入《使命名贤》中。洪熙元年,召入翰林,任修撰。《千顷堂书目·集部·别集类》著录其所著尚有《归田集》二卷,未见。《南夷书》记述元、明之际云南的主要历史事件,特别是明初平云南的三大征(—年),其情多得之于洪武年间作者在云南的耳濡目染。故其叙事条理清晰,行文朴实生动,史实和情节多有出乎他书记载之外者。由于该书乃追忆之作,兼之使者行箧少书未能详考,以致在述及人、时、事等处,难免间有失误。至如傅友德二次征南及沐英赐死等,也因其时讳言而缺略。但因作者生于其时,尚能亲闻当事人如张因、张荣祖等人的言谈,多少反映出当时人的一些看法,远非后世附会凿空之作可比,不失为研究明初云南的珍贵史料之一。爰就《明实录》、《明史》及有关史料为之笺注,阙略者笺补之,歧误者考校之,求其当而已。以为研究这段历史的案头检索之需。今传《南夷书》,仅见北京图书馆所藏明钞本一种。该本原为明天一阁藏书,阁主范钦嘉靖间曾为云南右布政使,故有是书。清乾隆三十八年浙江巡抚三宝采进四库馆,发还后不知何时流入坊间。年腾冲张荣廷在北京见之,因索价奇昂,钞录一本赠云南省图书馆,是为《滇钞本》,今云南省社科院、云南大学图书馆所藏,乃从省馆钞本过录的。此本较明钞原本虽略有脱误,但亦有所改正。今本文据北京图书馆藏明钞本,而以滇钞本校。书末附录三则:(一)《四库馆臣案语》。《总目提要》修改馆臣按语,往往馆臣是而《提要》非,故录以存真。(二)《滇钞本后记》。张荣廷关怀乡里掌故,跃然纸上,情不可没,录存之。(三)张洪《平缅录》。是录记述当日使缅往返情景,可为读此书之助,附录于后。是稿成于年,以为编写《云南各族古代史略》元、明部分之助。于今已廿余载、年迈古稀了!原稿直书,双行夹注;今改横行,注随段后。虽边钞边改,对原稿进行了修补,但仍有学力、精力两不逮者,徒增“学也无涯”之叹!南夷书(明)张洪撰 云南,古西南夷,汉昆明国①。昔有五彩云气见赵州②,时蒙氏建国于大理,在赵州南,遂以为国号③。今大理有云南县是也④。 ①《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长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则明永乐时的云南省境应包括古代的滇国、昆明国、夜郎诸国的极西部和邛都诸国的南端。此处只言昆明国,盖指云南西部洱海地区而言。 ②赵州州治在今大理市凤仪镇。洪武十七年将云南县改属赵州,此处即包括云南县而言。 ③国名南诏,郡名云南。《册府元龟》卷《外臣部·册封第二》说:“(开元)二十六年九月,封西南大酋帅蒙归义为云南王。” ④云南县。汉置。其地在今祥云县。蜀汉置云南郡,唐为姚州云南郡。其名不始于南诏蒙氏。惟云南地方有此传说,见元郭松年《大理行记》及明倪辂《南诏野史》。 蒙氏致祚于段氏①,更国号曰大理。元世祖以亲王统兵征伐,道吐蕃,略地南中。而段氏所居,地倚点苍山以为固,前临珥河②,表里环抱。段氏筑两关于险隘,名曰龙首、龙尾③。元兵不攻其间,乃潜行点苍山后,扳援而上,下瞰国中。段氏惊溃,遂降④。徙其治于昆明,仍其旧号曰云南⑤。 ①蒙、段二氏之间尚有郑氏大长和国、赵氏大天兴国及杨氏大义宁国。段氏盖灭大义宁国者,非直接承祚于蒙氏。详见李京《云南志略》、蒋彬《南诏源流纪要》、杨慎《滇载记》、倪辂《南诏野史》等书。 ②珥河,即洱河。今洱海。 ③《新唐书·南诏传》说:“开元末,皮逻阁逐河蛮,取太和城,又袭大厘城。守之,因城龙口。”《蛮书》卷三也说:“于时既克大厘,筑龙口城。”龙口城即龙首关,今上关。《蛮书》卷五说:“(龙尾城),阁罗凤所筑。”龙尾城即龙尾关,今下关。则龙口城、龙尾城乃南诏蒙氏所筑,非始于段氏。 ④程文海《世祖平云南碑》(在大理城西)说:“乃宪庙践祚之二年,…十二月,薄其都城,城倚点苍山、西洱河为固。国主段兴智及其柄臣高太祥背城出战,大败。又使招之,三返,弗听,下令攻之。东西道兵亦至,乃登点苍山,临视城中,城中宵溃。兴智奔善阐,追及太祥于姚州,俘斩以徇。”是大理国王奔鄯阐(今昆明),其相高太祥退守姚州。此云“遂降“者,盖终括之辞。 ⑤至元十二年立云南行中书省于中庆(《元史·地理志》作“十三年”,此从《怯烈传》),赛典赤以平章政事行云南中书省事,云南始为行省之名。自大理徙治中庆(今昆明)当亦在其时。此叙于赛典赤行省云南之前,未之深考。 世祖入继大统,分王其支子为云南王①。以其地近华阳黑水之域②,又改封为梁王③。而诸夷叛服不常,羁縻者四十余年④,号令不能及其人,乃以赛典赤为云南行省平章⑤。 ①《元史·世祖本纪》:“(至元四年八月)丁丑,封皇子忽哥赤为云南王,赐驼纽金镀银印。”忽哥赤乃忽必烈第五子。②《尚书·禹贡》:”华阳黑水为粱州。”华阳,华山之南。黑水,今金沙江,又名诺矣江。诺矣,彝语黑水。 ③《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二十七年)冬十月壬申,封皇孙甘麻剌为梁王,赐金印,出镇云南。”甘麻剌乃忽必烈长子朵儿赤之子。当忽哥赤之子也先帖木儿继为云南王时,又另封甘麻剌为梁王,并非改封,此文失考。惟梁王为一等王,云南王为三等王,可互为升降。如元末云南王忽哥赤之后把匝刺瓦尔密可进封为梁王,而梁王王禅之子帖木儿不花则降封为云南王。 ④自宪宗三年到至元十年赛典赤行省云南,才二十年耳!此云“四十余年”,亦未之深考。 ⑤事见《元史·世祖本纪》及本《传》。 赛公初下车,接见无虚日。虽以一壶浆至,必笑而纳之,更厚其酬答。由是远近翕然俱来。赛公度其可与语,乃告其民曰:“吾欲分尔耕,贷尔牛、种、耒耜、蓑笠之具,度亩收若干?”夷曰:“可得稻二石。”公曰:“输官几何?”夷曰:“半之。”公曰:“太重,后将不堪。其牛、种、耒耜之具不复再给,牛死买牛,具弊修具,一家衣食所须,半岂能给?”夷曰:“然则三分之一。”赛公曰:“尔虽克供,惧尔子孙弗继也。后之代我者,必欲盈其数,则上下相恶矣!吾与约。尔无我违;亩输米二斗,其勿逋!”夷大悦。或请曰:“租甚轻①,弗克致,奈何?”赛公又询其地之所宜,宜马则入马,宜牛则入牛,并与米直②相当;不产牛马入以银。今之粮折牛马、粮折银是也。赛公卒③,追封咸阳王,祠于学宫之傍④,民甚思之。 ①据支渭兴《中庆路增置学田记》所载,大理路赵州没官田双3角,租.6石。以每双折四亩计,则每亩租额约为稻1.6斗。而泰定二年《太华山佛岩寺常住田地碑记》所载,租额每亩约为稻3.1—5.8斗。则此文所云“亩输米二斗”当稻三斗以上,较之大理路官田租额为重,比中庆路(昆明地区)私田租额则稍轻。 ②直与值同。 ③赛典赤卒于至元十六年。 ④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一《云南府祠庙》:“咸阳王庙在郡学之西。” 继赛公者,不能遵其轨度,建昌、越巂皆叛。元兵屡出,辄败还。时有脱欢普花者,坐脱脱亲属,左迁云南省左右司朗中①。乃宣言曰:“夷易耳!惜我位卑不能用众也。”梁王闻之②,乃假脱欢平章以行,至则诸叛悉平。遂承制拜平章,累功封梁国公③。 ①脱欢普花,《元史》无考,见于柯凤荪姻丈《新元史·行省事相年表》、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一支渭兴《重修中庆路庙学记》:“今蜀国公角青荣禄大夫本省右平章知枢密院使脱欢普花,以世臣子孙,累践清要。至正乙未,由中书吏部员外郎,出为本省左右司郎中,升参政、右丞,以至平章政事。”至正乙未为至正十五年。《新元史·行省宰相年表》系其任平章政事于至正二十八年,盖据支渭兴《重修五华寺记》,题“荣禄大夫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脱欢普花纂额”,碑立于至正二十八年。 ②此梁王当为孛罗帖木儿。《平夏录》说:“天统二年(至正二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抵云南,梁王孛罗(原注:一名把都)及云南行省廉访司官先二日走。”《明太祖实录》卷十六作“甲辰(至正二十四年)春三月,胜兵至云南,元梁王孛罗帖木儿及行省廉访司官弃城,退保金马山。”是孛罗、孛罗帖木儿、把都为一人。 ③当据上引《重修中庆路庙学记》作“蜀国公”。惟下文屡称“梁公”,则此文作“梁国公”似非原文有误。何时改封,待考。 洪武四年,天兵平四川,驰檄谕之,使即降;否则,移师南指。梁王方游憩于五华寺,得檄,召梁公与之议。梁公曰:“敌人之言,未足深信。中国初定,未遑远略,此特以虚声恐我。即欲来,当潜师远袭,不宜使人豫为之备也。吾闻四川不守,贵州、建昌相继折入,则云南孤立无与,其为后日之忧乎?可使人因贵州降者觇其虚实,以为后图。”乃令罗罗①小镇抚为贵州圉人,牵马献。其小镇抚者颇黠慧,能夷书②,凡经过城邑守备,皆详志之。稍能言中国经制之略,归以告。王召梁公计之,公拊脾曰:“事去矣!王及臣俱老矣!当修贡称藩,得全首领归地,不敢谋后嗣也。”梁王以其说迂,不果来献。未几,梁公殁,王亦卒,嗣梁王立③,司徒答里麻秉政。 ①《云南志略·诸夷风俗》:“罗罗,即乌蛮也。”今彝族先民。 ②夷书,今彝文。 ③此梁王当为把匝刺瓦尔密,《明史》有传,误孛罗、把匝刺瓦尔密为一。《明太祖实录》卷71载洪武五年《谕云南诏》称“梁王把都”(即孛罗),卷92洪武七年八月《谕云南诏》已改称“梁王把匝刺瓦尔密”。则孛罗当卒于洪武五年至七年八月间。 时,国朝遣儒臣王子充为国信使①,问以不世见之故。答里麻留之。适鞑靼使从西番来,问何故与中国相通。遂杀子充,始绝意于朝献矣。是年,有白气从东方起,直拂西南。梁王以问威楚路知事某:“此何祥也?”知事密以兵形告,且曰:“必亡,惟偷旦夕之欢耳!”王以钱若干赐之,曰:“与尔取酒暂欢也。”既而,天兵讨之,实洪武十四年秋七月也②。命别将以舟师由蜀江泝流而上③。命颖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为左副将军,西平侯沐英为右副将军,率大军由贵州入,号三十七万④。 ①王祎字子充,《明史》有传。其事在洪武五年春正月,见《明太祖实录》卷71。 ②据《明太祖实录》卷及,乃八月“简练军士”,九月命将出师。此云“秋七月”,未详所本。 ③《明太祖实录》卷说:“分遣都督胡海洋等帅兵五万由永宁趋乌撒。”即此道之兵。④据《明太祖实录》卷所载,“凡二十四万九千一百人”,益以胡海洋所率五万人,故各书皆称“三十万”。此云“号三十七万”,未详,或当时传说如此。 初,梁王闻舟师来,命□□右丞①率境内罗罗,聚重兵于乌撒②,以扼吾师③。别命右丞观音奴觇贵州陆路□□有无④。观音奴遇永昌侯于普安,遂纳款,密受约束以归,报曰:“汉兵自蜀江来,贵州路不足虑也。”答里麻以为然,遂不设备。及大军至白水,夷始奔告曰:“汉人至矣!而控弦被甲者皆先生。”其俗辫发垂后,惟道士束发在顶,盖呼道士为先生也。答里麻沈吟久之,曰:“汉人何其多耶!先生且尔,况大军乎?”始部分为行计。将行交水以拒守,得胜兵万人。始即垒,吾之游骑已至,答里麻盖不知也。尝夜欲食镈饨⑤,庖人启门出汲,守者呵之,愿人鞭守者而出。既至河,见隔水游骑成列,乃惊仆,遂窃战士马驰还。故未败而云南先扰,时九月十一日夜也。翌日昧爽,蓝玉兵至交水,昏雾不见人,乃命衔枚从上游绝水而渡。即其垒,始呼噪驰入,斩馘殆尽。遂乘胜直抵云南,克之,实九月十四日也⑥。 ①疑缺”乌撒”二字,当作“乌撒右丞”。《弇山堂别集》卷85《大理战书附》载《总兵官征南将军檄示大理守土段信苴世》作“乌撒右丞石卜”,可证。或疑为“实卜”二字,与“右丞”倒置,作“右丞实卜”,似与缺字位置不合。②乌撒,今贵州威宁。 ③《明太祖实录》卷说:“时元右丞实卜闻都督胡海洋等兵进自永宁,乃聚兵于赤水河以拒之。及闻大兵继至,皆遁去。”④此处空文当为“汉兵”二字,作“觇贵州陆路汉兵有无”。下文“汉兵自蜀江来,贵州路不足虑也”,正承此言。 ⑤原本“镈”误“博”,今正。 ⑥此文前后两处月、日俱误。九月一日始于金陵誓师,何能于九月十一日即抵曲靖,如此迅速?据《明太祖实录》卷,破答里麻于十二月丙寅,为十二月十六日;《明史·太祖本纪》作“戊辰”,为十八日。而克昆明乃为癸酉之明日,即十二月二十四日。《实录》所谓“自秋九月出师至是百日,云南平”,亦系举其成数言之。 初,郑国公常茂见交水稻田中有乘马者陷入泥淖,冀得其马,挥刀斫之,其人呼曰:“我司徒平章也。”遂禽之。梁王保昆明池水寨以自固,闻答里麻败,云南失守,穷蹙,仰药死①,其众悉降。惟乌撒罗罗不散,连结各处土酋,据险相应,与云南迤西诸路皆不下。 ①《明太祖实录》卷说:“洪武十四年十二月壬申,把匝刺瓦尔密挈妻孥与左丞达的及驴儿,俱入晋宁州忽纳砦,焚其龙衣,驱妻子赴滇池死。把匝刺瓦尔密遂与达的、驴儿夜入草舍中,俱自缢死。”《明史·把匝刺尔密传》同。此文云“仰药死”,与史异。惟云南地方史有此说。王奎《平云南颂》说:“梁王闻败,弃城走晋宁,伏鸩卒。”《南诏源流纪要》也以为“自鸩”。《滇史》卷十作“遂仰药死”。“仰药”或即指“饮鸩”。惟程本立《黔宁昭靖王庙记》说:“柏匝刺瓦尔密闻达里麻败,遁滇池岛中,先缢其妃,而自饮药不死,投水死之。”《南诏野史》所记略同。此又一说,今并存之。 於是征南将军友德、左副将军玉引兵趋大理,右副将军英分兵还定乌撒①,留汝南侯梅思祖戍守云南②。夷人以为将轻师寡,各怀异志,暗相连结,同日俱叛。董知州以安宁州叛③,罗次、三泊④等处应之。摄赛⑤以东川叛,芒部、仁德府⑥等处应之,共推高宣慰为盟主⑦欲复梁王宗社,拔营宵遁,走安宁、罗次、邵甸、富民、晋宁、大棋、江悉众来攻云南⑧。时城中资粮器械殆尽,汝南侯欲弃城遁去,度不能令,复婴城固守。戍兵脔尸爨骨以供餔,裹创映堞以支敌。乃夜缒刘总旗出,访总兵所在求援。刘夜行昼伏,得至乌撒,见西平侯沐公言状。公遂提兵西援,遣人告云南固守,大军且至。其人夜闻更鼓,错诣高宣慰营,夷闻之,宵遁。城中见贼不出,以为有奇;及见鸟集其营,始知循去。乃资其馀粮以暂给。既而,沐公至,人心始宁。招降讨叛,军威复振。出者因粮于敌,居者为耕守计,始以客为主也⑨。 ①案;此时傅友德未尝引兵趋大理。据《明太祖实录》及《明史·太祖本纪》,洪武十五年闰二月癸卯,蓝玉、沐英进兵克大理。六月,沐英自大理还军滇池,会友德军,进击乌撒;蓝玉驻兵建昌。九月,云南诸夷叛。则是时友德、沐英在乌撒,蓝玉在建昌。本文所记失之。②《明太祖实录》卷:“洪武十五年二月乙卯,置云南布政使司,改中庆路为云南府。命汝南侯梅思祖、平章潘原明署布政使司事。” ③案:此时任安宁土知州者为董赐,不闻有叛。傅友德《与董赐书》说:“于时足下以前安宁知州来见于稠人之中,余目而异焉,遂加盼睐,仍试以事。继而招降抚顺,绥辑遗黎,颇著诚款,达官贵人咸称其能。于是乃复其任。使保妻子焉。壬戍(洪武十五年)春,乌蛮构衅,遗毒边境,余与诸将分兵致讨。时有大理起到土官高生等,悉寓桂城,欲俟途平,俾今朝觐。而阃帅不仁,失于抚字,致令惊疑,接踵而遁。及至本土,遂为仇雠,举兵相向,攻我城邑、杀我吏士,日甚一日,转加昌炽,阃帅莫制矣。足下介于群凶之中,确守岁寒之节。斥其奸谋,诛其来使,独挟妻孥,冒刃入滇。复与列校分守城垒,投放矢石,城之所以存者,预有功也。副将军西平侯闻难来赴,诛锄芟刈,群蛮复定。”是董赐不惟不叛,乃抗叛守城有功者。故于事定后,洪武十七年春正月,董赐升任鹤庆府流官知府,其继子董节袭任安宁州土知州。不闻安宁州另有董知州,此书所记恐误。 ④罗次,县名。今划入禄丰县。三泊,县名。在今晋宁县治(昆阳)西。⑤摄赛,东川府女土官知府名。 ⑥芒部,今镇雄。仁德,今寻甸。 ⑦或即上引傅友德《与董赐书》中之”高生”。 ⑧此云南乃指云南府城,今昆明。 ⑨《明史·云南土司传》说:“(洪武)十五年,友德等分兵攻诸蛮寨之未服者,土官杨苴乘隙作乱,集蛮众二十余万攻云南城。时城中食少,士卒多病,寇至,都督谢熊、冯诚等撄城固守,贼不能攻,遂连营为久困计。时沐英方驻师乌撒,闻之,将骁骑还救。至曲靖,遣卒潜入报城中,为贼所得,绐之曰:‘总兵官领三十万众至矣。’贼众惊愕,川等处,复据险树栅,谋再寇。英分调将士剿降之,斩首六万余级,生擒四千余人,诸部悉定。”《土司传》乃据《明太祖实录》卷成文,惟”连营”误作“远营”,“晋宁”误作“普宁”,”大棋”误作“大理”。今均据《实录》正。其所记应与此文同属一事,惟一作杨苴,一作高宣慰,未详其故。或二人同为叛者首领,记事者所取不同。 西师所至皆迎降,过则复叛。友德军于大理之龙尾关,扼险不得进①。夷人遗友德书,以为南中之事,当师法诸葛武侯,不留镇兵而财用足,求如孟获者立而击之。又贻诗诮之曰:“当今天下平犹易,自古云南守独难。”②友德命掾吏陈观为书报之曰:“武侯以区区梁州之众,抗六州之师,不留镇兵,力不足也。今以天下之力,举一方残破之余,其势不同也。吾陈于此,欲待尔降;不降,则一麾而渡耳。”夷得书,不报。遂鼓而进,万马浮河而渡。一骑先登,夷人围之数百重。骑振辔欲东,夷并力东御;即跃马向西,杀数十人。少止,复然,夷人莫敢当其冲者。遂突围出,出而复入。既而,诸骑毕登,夷大崩溃,遂克大理。分兵徇鹤庆、丽江、景东、蒙化,皆下之;金齿亦降③。乃班师④。 ①据《明太祖实录》、《明史·沐英传》及《云南土司传》所载,进兵攻大理者为蓝玉、沐英,友德未预斯投。此文所说。或据云南地方传说如此。亦见《滇载记》及《南诏野史》。抳,音旎(ni),‘止’的意思。 ②《南诏野史·大理战书》条:“洪武十五年二月,大理伪国段世闻滇破,差都使张元亨、州判李洪,自大理来下战书,略云:鄯阐危如登天,大理险倍投海。英如汉武习战,仅置益州;雄若元祖驻跸,只得鄯阐。取之易而守之难。不若依我。请乞册封,定为进贡,是为良策。吾实武人,不通经史,前代得失,则厌闻也。恭惟麾下振耀皇威,功不下于孔明,才克堪于方叔;涤山川之旧染,历代所未有也。吾与汝既无杀父之仇,又无财债之怨,无故交锋,真乃不祥。汝屯威楚,彼处之民有何罪焉?若耗人之食,是绝其命;取人之财,是刳其心;掳人妻女,是乱人伦,则予之应不得已也。爰念汝等皆中国之人,岂无一二达士,得此何益,不得何损。西南之地称为不毛,易动难安。今春气渐暄,烟瘴渐起,不须杀汝,四、五月间雨淋河泛,汝粮尽气敝,十散九死,形如鬼魅,色如黑漆,欲活不能,汝之进退狼狈矣。莫如趁此天晴地干,早寻活路,宁作中原鬼。莫作边地魂,汝宜图之。大理国段世顿首具。”书后一诗云:“长驱虎旅势威桓,深入不毛取暴残,汉武故营旗影灭,唐宗遗垒角声寒,方今天下平犹易,自古云南守独难,拟欲华夷归一统,经纶度量必须宽。”书后附短章乃大理国文例,见《桂海虞衡志》。乃《弇山堂别集》卷85《诏令杂考》—《信苴世诗》条,将诗倒置于书前。该书云:“前者专人敬诣辕门,获奉檄示,披诵再三,惶恐无地。所云`吾是武人,不通经史,前代得失,则厌闻也。愚闻先民有曰,囗荛之言,圣人择焉。况乎经乃载道之器,史乃记事之书,有天下者舍此其何拟哉!且夫武以定乱,文以守成,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不通之说,必谦退耳!”据此,则“吾是武人”四句乃傅友德《檄》中之语,故段世复书认为是其谦退之辞。《南诏野史》将其杂入段世所下战书中,未详所据。据上引及《滇载记》,《南诏野史·大理战书》乃其第二书。《滇载记》云:“明遣都使张元亨驰书颖川侯傅友德、西平侯沐英麾下曰:`大理乃唐交绥之外国,善阐实宋斧之余邦,难列营电,徒劳兵甲。请依唐宋故事,宽我蒙段,奉正朔,佩华篆,比年一小贡,三年一大贡。友德怒,栲辱其使。明再上书曰:‘汉武习战,仅置益州;元祖亲征,缘善阐,乞冀班师。’友德答明书曰:‘我大明龙飞淮甸,混一区宇,陋汉唐之小智,卑宋元之浅图。天兵所至,神龙助阵,天地应符。汝段氏接武蒙氏,运已绝于元世,宽命延息,以至于今。我师已歼梁王,报汝世仇,不降何待。’”《明史·云南土司传》即据此成文。惟本书所载与各书所载书意,均有所不同;而本书下文所载傅答书,亦与《滇载记》、《明史土司传》有异。盖各书所载,均为作者私意节录之文,原件如何?待考。③《明太祖实录》卷:“洪武十五年闰二月癸卯,征南左副将军永昌侯蓝玉、右副将军西平侯沐英进兵攻大理,克之。大理城倚点苍山,西临洱河为固。土酋段世闻王师且至,聚众扼下关以守。下关者,南诏皮罗阁所筑龙尾关是也,号为险要。玉等至品甸,遣定远侯王弼,以兵由洱水东趋上关,为犄角势,自率众抵下关,造攻具。遣都督胡海洋,夜四鼓由石门间道渡河,绕出点苍山后,攀木援崖而上。立我旗帜。昧爽,我军抵下关者望之,踊跃欢噪,酋众惊乱。英身先士卒,策马渡河,水没马腹,将士随之莫敢后,遂斩关而入。山上军望见,亦下攻之,酋兵腹背受敌,遂溃。拔其城,段世就擒。乃分兵取鹤庆,略丽江,破石门关,下金齿,由是车里、平缅等处相率来降,诸夷悉平。”《明史·云南土司传》据此成文,并云:“世与明皆段宝子也。” ④《明史·太祖本纪》:“洪武十六年三月甲辰,召征南师还,沐英留镇云南。” 诏立云南等处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①,分统典兵莅民之职。改路为府②,设官如内地。立云南左、右、前三卫于昆明。立曲靖卫于昆明之东,以接乌撒。立临安卫于建水州,以镇车里诸夷。立楚雄卫于昆明之西,又西为大理卫,大理之北为珥海卫③,西为景东卫、蒙化卫④,西南为金齿卫⑤,皆当百夷之冲⑥。时百夷未归聀方,故特为之备焉⑦。近则立安宁、杨林二千户所⑧,在昆明东西百里之内。凡九卫二千户所,以西平侯英总其师,得调四川、建昌、贵州三都司军马,以备缓急之援⑨。时叛乱之余,成兵残弊,爨僰之民⑩连被兵革,杀伤甚众,余皆鼠窜偷生,不事耕获,人甚饥。沐公乃大开屯田,军士秉耒耜者十七,执器械者才十三耳。乃益发人充其数,人益多,始增戍于未附之地。时越州土官龙海顽犷不率化[11],乃立越州、马龙[12]、平夷、普安、陆凉五卫,环其地以逼之。后徙者益多,乃立云南中、后二卫,木密关[13]、易门、易龙三千户所。 ①《明史·地理志》:“洪武十五年二月癸丑,平云南,置云南都指挥使司。乙卯,置云南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司治云南府。”②《明太祖实录》:“(洪武十五年三月己未),更置云南布政司所属府、州、县。” ③珥海即洱海。洱海卫在今祥云县境,当在大理之东。④景东卫、蒙化卫均当作大理之南。 ⑤上述各卫建立时间不一,此文盖概述各卫防御形势。⑥李思聪《百夷传》说:“百夷,即麓川平缅也。地在云南之西南,东接景东府,东南接车里,南至八百媳妇,西南至缅国,西北连西天、古刺,北接西番,东北接永昌。其种类有大百夷、小百夷,又有蒲人、阿昌、缥人、古刺、哈刺、缅人、结些、哈杜、怒人等名。以其诸夷杂处,故曰百夷。今百字或作伯、僰,皆非也。 ⑦《明太祖实录》卷:“(洪武十五年闰二月)乙已,置平缅宣慰使司,以土酋思伦发为宣慰使。”则是时不得谓之“未归职方”。惟明初对麓川的扩张作了具体的防备。《云南机务抄黄》载洪武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谕》中说:“遣官间问云南老人,皆说:‘死可伐地方三十六路,元朝时都设官,后被蛮人专其地,已四十年已近。因云南(梁王)、大理不和,其蛮又侵楚雄西南远干(今镇沅)、威远(今景谷)二府,梁王无力克服,至今蛮占。’以此观之,云南不可不备。”《明大祖实录》卷:“(洪武十八年十二月)癸丑,平缅宣慰使思伦发反,率百夷之众寇景东,土官知府俄陶奔白崖川,都督冯诚率师击之。”《云南机务抄黄》载洪武二十年五月十一日《谕》:“近日李原名自平缅归,联静听敷陈百夷事情,…皆百夷诡诈万端,虽数千万言,并无一语可信者。由此观之,此蛮夷甚有窥伺之谋,或早或晚,必有扰边之患。敕符到日,昼夜缉垒金齿、楚雄、品甸及兰仓江中道,务要城高壕深,排栅粗大,每处火铳收拾一二千条或数千百条。云南有造火药处,星夜煎熬,以备守御。”(亦见《弇山堂别集》卷87)《明太祖实录》卷:“(洪武二十年六月)庚子,遣通政使司经历杨大用往云南练兵。时百夷屡为边患,上欲发兵平之,先已敕西平侯沐英、指挥储杰等为筹边计。…大用至沅江等府,其土官请以兵五万听调。”又卷:”(洪武二十年八月)丙寅,遣右军都督佥事孙茂以钞三万二千锭,往四川市耕牛万头。时将征百夷,欲令军士先往云南屯田,预备粮储故也。”由于明初王朝政府从各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从而取得次年定边战役的胜利,奠定了云南边疆政治的基础。⑧杨林,在今嵩明县东境。 ⑨《明史·沐英传》:“明年(洪武十六年),诏友德及玉班师,而留英镇滇中。” ⑩元代称大理国的军队为“爨僰军”后为云南乡兵,亦作“寸白军”。此文“爨僰”亦系泛指云南内地少数民族。[11]越州,元置。在今曲靖市南境。《明太祖实录》卷:“越州,夷言苦麻部。元末,龙海居之,部属俱罗罗种。王师征南时,英驻兵其地之汤池山,谕降之,龙海遂遣子入朝,诏以龙海为是州知州。寻即为乱,英以计擒之,徙居辽东,至盖州病死。阿资继其职。” [12]“马龙”当作“马隆“。州名马龙,卫名马隆,宜分别之。[13]《明太祖实录》卷:“(洪武二十三年夏四月)辛酉,置木密关守御千户所于寻甸军民府之甸头易龙驿。” 二十一年,百夷王思伦法遣其酋刀斯郎寇定边县①,众十五万。西平侯沐英率兵御之,选战士得万五千人,与之对垒②。夷人驱象以战,马惊走,不得成列。公患之,令其下曰:“谁与我当③象?”总旗刘安西奴请往。时夷人隔水陈象,激其怒号以恐吾众。安西奴以五人赴之,斫一象鼻而回。被伤象反走,馀象惊奔不可制,夷人夺气。公赍以白金百两、马一匹,承制拜百户。公喜曰:“吾知破象之术矣!以火攻之,必克也。”又曰:“吾欲知其虚实,谁与我执夷人讯之。”一卒曰:“诺。”即渡水挟一人以归。问其善斗者为谁?曰:“刀斯郎所将皆悉刺也。”夷人以敢死士为悉刺。曰:“其居何所?”夷指平地象多者曰:“此即其营。”又曰:“左右两山夷虽众,然能战者少也。”公慰劳遣之。乃命左卫指挥马骥张左翼,以攻其左;右卫指挥金仁张右翼,以攻其右;亲率前卫指挥张因等,直赴刀斯郎营。火枪、火箭一时俱发,象惊俱、却走,自招蹂践。刀思郎大败,追及斩之。左阵稍却,命掠阵者所马骥首,骥赴敌死。公挥兵救左翼,得全其师。自是夷震惧,不敢复出矣④。乃遣千户郭均美往谕,期以明年大举伐之。思伦发惧,遣使乞降⑤,以其地为麓川宣慰司,以思伦发为宣慰使。思伦法乞于麓川下加平缅二字,从之。时百夷岁欲侵缅国,以并其地,朝廷盖不知也⑥。 ①定边县,今南涧彝族自治县。 ②《明太祖实录》卷,“时思伦发悉举其众号三十万、象百余只,复寇定边,欲报摩沙勒之役,势甚猖獗。新附蛮夷,阴相连结,咸蓄心。西平侯沐英知夷人反侧,…乃选骁骑三万,昼夜兼行凡十五日,抵贼营,与之对垒。”《实录》所记人数,恰为本书所说“众十五万、”万五千人”之倍。盖本书所说为实数,《实录》所记为虚数,明代纪录往往如此。详见魏源《圣武记》卷12《掌故考证》。 ③“当”,原本作“尝”,误。据滇钞本正。 ④定边之役详情可参见《明太祖实录》卷(洪武二十一年三月甲辰)条,《明史·土司传》及《沐英传》之文悉本之,惟《沐英传》误作二十二年事。本书所记与上述诸书略异,盖本之千户张荣祖所说。张荣祖与张因曾“率骑士乘胜追奔,直捣其栅寨,破之”(见《实录》),直接参与此次战役,则其言不为无据,可补史缺。 ⑤据《实录》及《明史·土司传》,注谕者乃杨大用。《明太祖实录》卷:“(洪武二十二年十一月己亥),命通政使司经历杨大用使百夷。初,百夷思伦发寇摩沙勒及定边,西平侯沐英率兵讨之。思伦发凡再拒战皆败,乃遣其把事招纲等至云南言:`往者叛逆之谋,实非己出,由其下刀厮郎、刀厮养所为。乞贷其罪,愿输贡赋。云南守臣以闻。上乃遣大用赍敕往谕思伦发曰:`(前略)独尔思伦发效尤梁王,纳我逋逃,又数年矣;金齿、景东之役,皆尔所致。联谓尔欲图人民、广土地,与中国较胜负,故敢数生衅隙。继命诸骁将率师屯营,且耕且守。今尔来诉:‘往者犯边之罪,不由于己,皆刀厮郎等所为。’未审其果然否?尔虽声言归诚,于心实怀不轨。果若此,何以释我诸将之愤乎?如欲释愤,当躬修臣礼。悉偿前日用兵之费,则麓川无问罪之事,土酋各保世禄。不然,则旌麾所向,丑类为空。大用既至麓川,思伦发听命,遂以象、马、白金、方物入贡谢罪。大用复令思伦发追获云南逃去叛贼自处等二人、把事刀厮郎等一百三十七人。百夷遂平。”郭均美曾于洪武十四年使麓川(《百夷传》)。洪武二十七年往赐“思伦发公服、幞头、金带、象笏”的“千户郭均英”(《明太祖实录》卷及《明史·土司传》),或亦“郭均美”。则郭均美也可能参与此次出使。 ⑥此说误。洪武十五年即以思伦发为平缅宣慰使,见前注。《明大祖实录》卷:“(洪武十七年八月丙子)…改平缅宣慰使司为平缅军民宣慰使司。仍以思伦发为宣慰使。(甲午),改平缅军民宣慰使司为麓川平缅宣慰使司。麓川与平缅连境,元时分置为两路,以统领其所部。至是,以思伦发遣使来贡,乃命兼统麓川之地,故改之。”且平缅宣慰司乃元代所置,《元史·顺帝本纪》:“(至正十五年八月戊寅)云南死可伐等降,令其子莽三以方物来贡,乃立平缅宣慰司。”是思伦发已袭任平缅宣慰使,至是始兼统麓川宣慰司地,而非“于麓川下加平缅二字”。张洪以永乐四年使缅,不知何以致误若斯。或其以“平缅”二字误连思伦发侵缅事,而行箧乏书,一时未之详考。 二十二年①,东川土官摄赛复叛。朝廷命靖宁侯叶昇讨之;以云南都指挥使宁正为副,率云南兵以往②。昇至牛览江③,夷人拒险,不得进。梦神人告曰:“惟能可渡。”昇寤,求将校中名能者,弗得。忽自悟曰:“必都指挥瞿能也④。”时能分兵攻别种蛮,忽追至,以所梦告之。能欢曰:“诚易耳!”令军中伐木造舟,以绐夷人;乃潜于上游缚枪为桴,下载牛皮浑脱,宵济之。夷不之觉,尽杀守江者以渡。既逾险,夷人相连结深沟高垒自固。声言出降,实无降意。公遣逻卒⑤,要其往来者杀之,夷人声势不相属,力屈者先出降。乃施降者令转相招致,稍稍相继出。然弥山漫埜错杂相连,不肯受笼络。昇与能谋,立栅堑为城郭,植营表□⑥街衢,移墟落市井⑦于其间,以相交易,使夷人得占地作家室。千户张荣祖权署东川府事,和辑诸夷,夷惧,不肯入栅。昇复遣人为盗,窃取马牛杀食之,或举其橐中装。夷诉之,昇佯为求盗,弗得,谕入栅避盗,夷稍稍居栅中。昇虑反复,欲掩杀之,惧弗克。乃令军士入山伐木,俾人丁壮者各负木,赴军垒营己屋。先令军中曰:“夷负木入垒,即缚之,塞其口;必尽缚,始悬白旗。各垒旗尽悬,闻信炮,即尽杀之。”是日,杀降者二万余人,夷丁壮俱尽。乃分系老弱妇女,尽取其金帛,始旋师。(以下为原本小注)张行人曰:靖宁侯之杀降也,岂不惨哉!予戌□⑧南,盖闻之千户张荣祖云。靖宁以杀降,后四年,坐党与伏法,瞿能亦及;其子弟尽杀锋镝之下,天之报复不远矣!二子岂不知长平之事,祸不旋踵,顾肆然为之而不知惧,无亦人欲胜而天理灭耶?权家爱胜,取鉴在斯! ①当作“二十一年”,见《太祖实录》卷—。 ②《太祖实录》卷:“(洪武二十一年六月甲子),西平侯沐英奏:‘东川诸蛮据乌山路劫寨而叛。其地重关复岭,岩壁峭险,上下三百余里,人迹阻绝。请讨之。’上乃命颖国公傅友德仍为征南将军,英为左副将军,普定侯陈桓为右副将军,景川侯曹震为左参将,靖宁侯叶昇为右参将,统领马步军往讨之。”又卷:“(洪武二十一年秋七月)丁酉,遣使赍敕谕征南将军颖国公傅友德等曰:‘东川、芒部诸夷种类虽异,而其始皆出于罗罗。厥后子孙蕃衍,各立疆场,乃易其名曰东川、乌撒、乌蒙、芒部、禄肇、水西,无事则互起争端,有事则相为救援。…其地山势险峻,道路崎岖,林箐深邃,其人与猿猱无异。大军一至,窜入林薮,倅难捕获。宜且驻兵屯种,待以岁月,然后可图也。’(戊戌),复遣使谕征南诸将曰:“……今征东川,其乌撒、芒部诸蛮,外虽服从,中藏狙诈。…龙海之蛮奸诡尤甚,水西恐与贼阴谋,皆须防闲,有备无患,切宜慎之。”又卷:“洪武二十一年八月壬寅朔,西平侯沐英调都督宁正帅兵会颖国公傅友德军,讨东川。……(九月)甲午,景川侯曹震、靖宁侯叶昇领兵分讨东川叛蛮。”又卷:“(洪武二十一年冬十月)丁未,征南右参将靖宁侯叶昇等进兵讨东川,平之,捕获叛蛮五千五百三十八人。”则此次征南之战乃是平定川、滇、黔彝族土司统治地区,亦即所谓彝族“六祖”支系统治中心地区的叛乱,东川之役仅是其中的一部分。战事仍以傅友德为主帅,沐英、陈桓为副,曹震、叶昇分师,而叶昇是平定东川的主将。云南都指挥使宁正是奉沐英之命,率云南兵会合叶昇作战,亦即所谓“会颖国公傅友德军”也。 ③今牛栏江。 ④万历《云南通志》卷九《官师志·名宦》:“瞿能…洪武二十五年,升中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掌云南都司事。”则此时尚未任都指挥使。 ⑤“卒”,原本误“率”.据滇钞本正。 ⑥原本空一字,疑为“作”字。 ⑦“井”,原本误“并”,以意正。 ⑥原本空一字,疑为“滇”字。 是岁,广西①夷者满、以情合兵叛②,同寇宜良。西平侯以都指挥汤昭率兵御之,戒其勿战,以待东川兵至。指挥高彬见蛮人压垒而陈,言于昭曰:“见可而进,兵之令图,战必克也。”昭止之,不从。彬出战,蛮败走,追之。昭闭营不出,蛮见我兵无援,悉众围。彬且战且却,得及浮桥以渡,余众溺死者有十七八③,报至,云南大恐,益发兵守浮桥。既而,东川兵至,西平侯亲往击之,磔者满、以情而归。始立宜良守御千户所,去云南九十里④。时叛者相次芟夷,惟越州龙海未下,西平侯以术致之,缚送京师⑤,其子阿资益肆凶忿,为普安、越州患⑥。二十四年,西平侯亲往征之,值霖雨弥月,士病湿肿,弗克穷索,还⑦。 ①原本脱“西”字,据王景常《黔宁昭靖王祠堂碑》、程本立《黔宁昭靖王庙记》、万历《云南通志》卷九《官师志·名宦·沐英》传补。 ②万历《云南通志·沐英传》说:“(洪武)二十一年冬十月,广西阿赤部酋长者满、矣情结越州土酋阿资叛。英自将直捣阿赤部,者满、矣情皆服诛,俘男女五千余口,马牛如之,阿资降。”惟《太祖实录》卷说:“(洪武二十一年十二月),是月,越州叛酋阿资等庇众寇普安,烧府治,大肆剽掠。征南将军颖国公傅友德等率兵击之,斩其营长者满、己青。”按:“者满己青”当即“才满以情”或“者满矣情”。程本立《黔宁昭靖王庙记》:“广西阿赤部叛,自将讨之,诛其酋曰者满、曰矣情。”则“者满”、“矣情”分别为二入名。广西,府名。府治在今云南省泸西县。 ③当作“十有七八”。 ④《太祖实录》卷:“(洪武二十三年五月)戊申,置宜良千户所。宜良去云南布政司百里,西平侯沐英遣千户许文、吴善等领兵镇守。文等乃筑城堡,控制诸蛮,屯田以给军饷,民皆悦服输赋。”此“百里”盖举其成数而言。 ⑤事见前“越州”注。 ⑥《太祖实录》卷:“(洪武二十二年春正月乙未),征南将军颖国公傅友德等复击走叛酋阿资,土官普旦来降。时阿资退屯普安,倚崖壁为寨。友德以精兵蹙之,蛮众皆缘壁攀崖,坠死者不可胜数,生擒一千三百余人,获马牛羊五千三百余头。阿资遁还越州。(二月)是月,西平侯沐英遣都督宁正,从颖国公傅友德击阿资于越州,败之,斩其党火头弄宗等五十余入,获马牛羊以千计。阿资势穷蹙,与其母请降。初,阿资之遁也,扬言曰:‘国家有万军之勇,而我地有万山之险,岂能尽灭我辈?’英乃请置越州、马隆二卫,扼其冲要,又分兵追捕。至是势穷,遂降。三月庚午朔,遣使命征南将军颖国公傅友德等还军,分驻湖广、四川卫所操练。”则征南之役于此基本结束。 ⑦《太祖实录》卷说:“(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辛已,越州土酋阿资复叛,命以前军都督佥事何福为平羌将军,同指挥王度将兵征之。兵至越州,官军进攻连捷,俘获甚众。会连月淫雨不止,山水泛溢,阿资援绝,与其众降。福择旷地置栅以处其众。西南有木蓉箐,实蛮人出没之所,复调普安卫指挥刘玉领兵置宁越堡镇之。”(亦见《明史·土司传》)《实录》未云沐英“亲往征之”。程本立《黔宁昭靖王庙记》说:“阿资复叛,自将讨之,击于补冲,杀获其众殆尽,阿资仅以身免。方搜捕山间,俄有旨谕王还镇,以前军佥都督何福为平羌将军,宁正为参将,代领其兵。阿资遣其子诣王降。王请于朝立卫越州。遂罢兵。”述其经过较详。 二十五年①,西平侯沐公卒②。都司以闻,朝廷哀悼之,追封黔宁王,谥昭靖,祠于云南③。初,云南既平,以省库银万两赐之④。王貯于布政司库,惟赏赍夷人得用,至是存者六千余两。嗣子后军都督春来迎父丧⑤,始辇归。诏以云南都指挥使宁正为右军左都督、佥都督冯诚为右都督、何福为左同知,徐司马为右同知⑥,以继西平之任。未几,以其子春嗣侯爵,来继父任⑦,罢宁正、何福掌都司事⑧,冯诚出镇大理。设提刑按察司⑨。二十六年,诚赐死,宁正入掌右军都督府,以佥都督瞿能同何福掌都司事⑩。始封眠王于云南[11]。初,黔宁以云南益[12]平,乞封建同姓,乃封靖江王于大理,寻以罪徽[13]。黔宁□□□□[14]其地,为夷汉所服,益不自安,凡姬侍有所出,即遣还京师,请封建益力,故有是命。乃立云南左、右、中三护卫,以云南后卫为广南卫、中卫为兰沧卫[15]。 ①原本误作“三十五年”,据滇钞本正。 ②《太祖实录》卷说:“(洪武二十五年六月)丁卯,西平侯沐英卒。…英旦视事于府,忽疾作,遽起还第,两足痹不能行,舁归就寝而卒,年四十八。”万历《云南通志》卷九(沐英传)作“二十五年五月十七日得末疾卒,年四十七”。“五月”盖“六月”之误,《滇史》卷十正作“洪武二十五年六月十七,西乎侯沐英卒,年四十七”,可证。此云“四十七”盖足岁,虚岁“四十八”。程本立《黔宁昭靖王庙记》作“一日暴薨,二十五年夏六月丁夕日也”(《滇史》卷十同)。所谓“忽疾作”、“末疾”、“暴薨”,在当时未易言也。刘崑《南中杂说》谓“子独不闻尽忠楼乎?黔宁父子赐药、赐缳,三世接踵,熟谓高、成二祖不防滇南、疑沐氏乎?”刘氏熟知滇南掌故,其说可信。 ③程本立《黔宁昭靖王庙记》说:“明年,太常以太牢祭王功臣庙,而云南父老、诸酋首合辞,愿立庙祀王。守臣奏请,上可许之。又明年,庙成。”万历《云南通志》卷12《祠祀志》:“黔宁王庙在府治南,洪武二十七年建。” ④《太祖实录》卷:“(洪武二十二年冬十月)丁已,西平侯沐英自云南来朝。上劳之曰:`自汝在镇,吾无西南之忧。锡宴于奉天门,赐黄金二百两,白金五千两,钞五千锭,文绮一百疋。又赐钞一万锭,令起第于凤阳。寻遣还镇。”“钞五千锭”,《明史·沐英传》误作“钞五百锭”。万历《云南通志》卷九《沐英传》和“钞二万五千贯,…别赐钞五万贯,使建第于乡”;程本立《黔宁昭靖王庙记》总叙“钞为贯凡七万五千”,则明初钞一锭为五贯。据本文所说,则此次赏赐主要为云南库银。 ⑤《太祖实录》卷:“(上)命其子春迎丧还葬。…冬十月八日,春奉柩至京师,遣中使临祭。后十三日,诏追封黔宁王,谥昭靖,赐葬于江宁县之长泰北乡。” ⑥《太祖实录》卷:”(洪武二十五年秋七月)庚寅,以云南都指挥使宁正为右军都督府左都督,命镇守云南。以左军都督佥事冯诚为右军都督府右都督,与都督佥事何福同署云南都指挥使司事。”又卷:“(洪武二十六年春正月辛亥),中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徐司马卒。司马,御赐名。字从政。世为扬州人。…十九年正月入觐,中军都督佥事。二十五年冬,率师征越。还,至成都,以疾卒。”则徐司马尚未莅此职。 ⑦《太祖实录》卷:”(洪武二十五年冬十月乙亥),命故黔宁昭靖王沐英子春袭封西平侯,往镇云南。” ⑧上书同卷:“(洪武二十五年冬十月乙亥),命镇守云南都督宁正署云南都指挥使司事,召都督佥事何福等还京。”又卷:“(洪武二十六年春正月)戊申,遣使召署云南都指挥使司右军都督宁正还朝。” ⑨《太祖实录》卷:“(洪武三十年正月壬申)。初置云南提刑按察司。以陕西按察司使张定为按察司使。”“张定”,万历《云南通志》卷九《官师志·题名》误作“陈定”。该《通志》卷五《建设志》载《都督同知沐建(云南等处提刑按察)司公廨记》则说:“洪武二十九年,太祖高皇帝有诏,开设云南等处提刑按察司,始即昆明县治为之,堂阶、门庑,制度粗备。”(实录)所据盖晚到之文。而本文叙之于二十六年前,乃连带书之,非准确时日。 ⑩《太祖实录》卷:“(洪武二十六年五月乙卯),命署四川都司事中军都督佥事瞿能署云南都司事。”又卷:“(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丑),越州土酋阿资复叛,西平侯沐春、都督何福等率兵讨之。”何福于二十五年奉诏还京,何时还镇?未详。 [11]《太祖实录》卷23O:“(洪武二十六年),是岁建珉王府于云南。”又卷:“(洪武二十七年冬十月)己丑,罢建岷王宫殿。”又卷:“(洪武二十八年夏四月己巳),敕岷府西河中护卫并仪卫司官军校尉往云南镇守,赐钞四万锭。”又卷:“(九月)甲午,诏岷王之国云南。……初,岷王定都岷州。上以云南土旷人悍,必亲王往镇之,故命岷王改都焉。” [12]“益”字疑是”夷”字音误。 [13]《太祖实录》卷:“(洪武二十五年春正月辛亥),靖江王守谦薨。…守谦既至云南,复奢纵淫佚,掠杀不辜,黩于货财,豪夺暴敛,号令苛急,军民怨咨。上犹不忍治罪,仍召还,安置凤阳。虽在贬斥,横恣自如,强取牧马,暴扰一乡。乃召至京,笞而禁锢之。至是卒”。 [14]原本空四字,未详。 [15]《实录》系于洪武二十八年,此盖连带书之。《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六年夏四月癸酉),置云南中护卫,调长沙卫将士守之。”又卷:“(洪武二十八年夏四月己巳),敕岷府西河中护卫并仪卫司官军校尉往云南镇守。”又卷:“(洪武二十八年九月)甲午,诏岷王之国云南。改西河中护卫为云南中护卫,调指挥同知贺安掌之;云南左卫为云南左护卫,指挥佥事王福掌之;云南前卫为云南右护卫,指挥佥事李谦掌之。……壬子,谕西平侯沐春曰:‘前改云南左、右二卫为护卫,盖此二卫官军久居云南,习于征战;若为护卫,则不可调遣,宜仍其旧。可改马隆卫为左护卫,余军置马隆卫千户所,分调越州卫官军补之;景东、蒙化二卫,以一卫为右护卫。调云南中卫于北胜州,置澜沧卫;云南后卫于广南府,置广南卫。’” 二十七年冬,西平侯春将讨叛酋阿资。以其与各处土官交通,兵至则走匿,致穷讨弗获①。乃徵各酋随征,令曰:“毋匿叛人阿资,违者族。”各酋既就徵,恐及,戒其地弗纳。阿资既无所往,乃散其众入草莽分窜,伺官军过,复聚。侯命分兵为千队,棋布络绎,若搜雉兔然。二十八年春,获阿资,烹之。其地悉平②。 ①《太祖实录》卷:“(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丑),越州土酋阿资复叛。西平侯沐春、都督何福等率兵讨之,营于越州城北,督指挥李得、徐毅分道四面攻之;又别遣指挥何琪、俞辅领壮士伏于歧路。以兵挑战。于是蛮寇悉众以出,伏兵四起纵击,大败之,杀获甚众,惟阿资脱身逃去。”《明史·沐春传》说:“阿资复叛,与何福讨之。春曰:‘此贼积年逋诛者。以与诸土酋姻娅,辗转亡匿,今悉发诸酋从军,縻系之,而多设营堡,制其出入,授首必矣。’遂趋越州,分道逼其城,伏精兵道左,以赢卒诱贼,纵击,大败之。阿资亡山谷中。”可与本文相参证。 ②《太祖实录》卷:“(洪武二十八年春正月)甲子,西平侯沐春、中军都督佥事何福等讨越州阿资,平之。初,阿资遁去,时曲靖土军千户阿保、张麟所守之地,与越州相接,其部属多与之贸易。春使人阴结阿保等,令觇知阿资所在,于其所经行之地,星列守堡,绝其粮道,阿资困急。福潜引兵屯赤窝铺,遣百户张忠等捣其寨,擒阿资,斩之。俘其党,越州遂平。”《明史·沐春传》说:“遂擒阿资、并诛其党二百四十人。”万历《云南通志》卷九《官师志·沐春传》也说“斩其首以徇”,《明史·云南土司传》一据《实录》成文,均与此文异。 二十九年,兰沧卫①指挥王佐言:“永宁州②土官阿乌诉其下卜八如甲率众叛去,乞加剿戮。”初,卜八如甲与阿乌不相能,以其众投入四川盐井卫③,指挥皇甫霖以为慕义来归,请以为土军千户。都督何福以王佐之言为然,率兵诛之。盐井卫分兵守其地,福并诛之。遂以其兵攻叛臣贾哈喇别寨,其子白塔佯为无备,请降;伺官军食尽,据险以扼其归,全军复没④。皇甫霖并其事以闻,诏切责何福,俾讨贾哈喇以赎罪;且命西平侯春、都督能⑤助之。三十一年春二月,师至兰沧卫,贾哈喇以其众诣都督徐凯降⑥。西平侯乃移兵金齿,为百夷声援。 ①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4《澜沧卫军民指挥使司·建置沿革》:“澜沧,旧无建置,洪武二十九年始于北胜州治之南筑城为军民指挥使司,领北胜、永宁、蒗蕖三州。”“澜沧”或作“兰沧”。治所在今永胜县。 ②万历《云南通志》卷4《地理志·永宁府沿革》:“古名楼头赕,地接吐番,又名答蓝。么些蛮祖泥月乌逐出吐番。遂居其地。……至元十四年置答蓝管民官,十六年改置永宁州,属北胜府。皇明洪武中属鹤庆府,二十九年改属澜沧卫。永乐四年升为府。”治所在今宁蒗县。 ③《明史》卷《四川土司》一:“盐井卫,古定笮县也。元初为落兰部。至元中,于黑、白盐井置闰盐县,于县置柏兴府。洪武中,改为柏兴千户所,旋改盐井卫。”治所在今四川盐源县。 ④《太祖实录》卷:“(洪武二十九年十二月),永宁州土贼卜八如加等劫杀军民,前军都督佥何福遣指挥李荣等领兵讨之,其子阿沙遁入革失瓦都寨。官军赍三日粮,深入追之。会天大雪,众饥疲,贼据险不下,军乃还。”《明史》卷《云南土司传》叙此事即据《实录》成文,惟“大雪”作“大雨”,揆之当地气候,疑作“大雪”是。《实录》谓“军乃还”,《明史》作“引还”,与此文异。此文言“全军复没”,恐差得其实,《实录》与《史》盖讳言败。 ⑤即瞿能。 ⑥《太祖实录》卷说:“(洪武三十一年二月)甲辰,都督佥事徐凯等平卜木瓦寨,执叛酋贾哈喇,送京师诛之。贾哈喇,么些土豪也。初,王师克建昌,授以指挥,俾领其部落。后与月鲁帖木儿叛。走据卜木瓦寨。其地峻险,三面斗绝。下临大江,江流悍急,不可行舟,惟一道仅可通人行。官军至,辄自上投石,遂为所扼,不得进。及是,凯等至,断其汲道以困之。寇不得水,日就穷促。凯乃督将士直抵其寨,力攻之。寇不能支,遂就擒。”《明史》卷《四川土司传》述此事亦据《实录》成文,均与此文异。 初,百夷未附之时,其王思可法卒①,子幼,弟代立,是为思瓦法,刑政不常,田游无度。陶孟②某弑之,求思可法之子立,是为思伦法③。陶孟以其女妻之,后被讨伏诛④;思伦法德其立己,且悯其死,遂举其女于故妻之上,号曰昭曩⑤犹中国称王妃。惟其言是用。夷俗:新君立,则土酋各献其女备内列。曩怙宠而,凡一女进,则诬其女以叛,思伦法辄徵而诛之,并缢杀女,弃尸麓川江⑥中。见者怜其冤,且忧及己,相次以待死。复徵木邦酋长刀干孟⑦,不赴,起兵伐之,败绩⑧。刀干孟遂连结各处以叛,攻宣慰司,拔之。思伦法走金齿,限潞江不得渡,棲于高良工山⑨。其属虎都沙⑩率腾冲旧汉人[11]为之捍蔽,使人来求援[12]。刀干孟亦因景东卫求自白,西平侯以闻[13]。 ①《永昌府文征·记载》卷2译傣文史书《麓川思可法事迹》:“当傣历五百十八年顷(公元年,当宋绍兴二十七年),罕芳为麓川土司。传至罕好,好传子罕静法。静法卒,无子,文武四人管理地方。因不可一日无君也,祷告天地,将放四马出城,视马所往且为下拜者,奉为主。祷毕,纵马,马绕城三匝而去。过湖畔,有为人牧羊者,名日刹远。四马跪其前,大头目趋候,告以天命,迎归,招为婿,奉之为主。刹远欣然受之,建城于蛮海,时傣历六百零二年(公元1年)也。刹远在职,称思可法,思之言白虎,可之言获,法之言王。刹远在湖畔牧羊,曾擒获白虎,故以为号焉。可法在土司位四年,迁居者阑。又四年,名声大振,中国、缅甸两面进兵来攻,不能克,中、缅兵各退去。是时思可法年四十五。因中、缅攻者阑不克,邻近闻之,相率纳贡,有曼谷、景线、景老、整卖、整东、车里、仰光诸土司至。思可法年六十六岁,是年生肖属鼠,又从者阑迁居达木城。傣历六百四十四年(公元年),思可法卒,年八十五岁。子思炳法嗣位。”案:此篇傣文史书如汉译文不误,殆后人追记之作,因已有曼谷、仰光之名;其中错误不可究诘,今略举之如下。该译文以为思可法乃获白虎王之意,解释说:“思之言白虎,可之言获,法之言王。”若以此解释为是,则据傣语语法,当为法可思,而不应作思可法。盖傣语动词在名词前,而限定语词在被限定词之后。由此可知其说之误。况傣语称王为“召法”,闽、广方言译为`绍华”。召、绍为“王”之意,法、华为“天”之意,合为“天王”,今此书译法为王,亦误。又该书以思可法之立在傣历六百另二年,是年当宋嘉熙四年(年)。据《元史·顺帝本纪》:“(至正二年十二月)以兵讨死可伐(思可法)。”则思可法活动年代应在元末,距宋末且百有余年,是思可法已成为百岁以上老人?据该书记载,思可法立后八年为四十五岁,则其立年为三十五岁;卒军八十五岁,当做傣历六百四十四年,则距立年傣历六百另二年才四十二岁,而该书述其在位四十八年,此纪年与在位之年亦不合。今以此《事迹》常为时人所乐道,而习焉不察,故录之以备一说,并略为考辨如上。李思聪《百夷传》说:“元祖自西番入大理,平云南,遣将招降其酋长,遂分为三十六路、四十八甸,皆设土官管辖,以大理金齿都元帅府总之。事有所督,则委官以往,冬去春回。至正戊子,麓川土官思可发数有事於邻境,诸路以状闻。乃命搭失把都鲁为帅讨之,不克而旋。遂乘胜并吞诸路而有之,乃罢土官,以各甸赏有功者。然犹惧再举伐之,於是遣其子满散入朝,以输情款,遂寝而不问。虽纳贡赋,奉正朔,而服食器用之类皆逾制度,元不能制。百夷之强始于此。”《元史·顺帝本纪》:“(至正十五年八月戊寅),云南死可伐等降,令其子莽三以方物来贡,乃立平缅宣慰司。”《百官志》同。“莽三”即“满散”之异译。 ②傣语“孟”为“平坝”或“邦”之意,称母为“陶”,“陶孟”犹言“一邦之母”,是傣掸族的官称。李思聪《百夷传》说:“叨孟总统政事,兼领军民。多者总统数十万人,少者不下数万人。“叨孟”即“陶孟”之异译。 ③李思聪《百夷传》说:“思可发卒,子昭并发代为宣抚。八年,传其子台扁。一年,昭并发之弟昭肖发杀台扁而自立。逾年,而盗杀之,其弟思瓦发代立。壬戍冬,其部属答鲁方、刀斯郎、刀泼郎等杀思瓦发,而立其侄,即满散之子思伦发也。”据此,则思伦发乃思可发之孙,而非其子。李《传》又说:“洪武辛酉,天兵南下,犹负固未服。总兵官西平侯沐英遣部校郭均美往复招徕,于是不烦兵而纳款内附。朝廷推怀柔之恩,乃授思伦发为麓川平缅等处军民宣慰使司宣慰使。”而钱古训《百夷传》说:“洪武辛酉平云南。明年,思瓦发寇金齿。是冬,思瓦发略于者阑、南甸。其属达鲁方等辄立满散之子思伦发,而杀思瓦发于外。”案:洪武辛酉为洪武十四年,其明年为十五年。据《太祖实录》卷:“洪武十五年闰二月乙已,置平缅宣慰使司,以土司思伦发为宣慰使。”则思伦发已于是年闰二月以前即已为“土酋”,何待于“是冬”“辄立”呢?钱《传》恐误。惟平缅宜慰使司改建为麓川平缅宣慰使司事在洪武十七年八月,见《太祖实录》卷及《明史·云南土司传》二。李、钱二人于洪武二十九年使缅及百夷,盖据当时名称述之。 ④此言陶孟被讨伏诛。 ⑤“昭”与“召”、“绍”之异译,意为王。“曩”为傣族贵族妇女之称。原本作“囊”,下文作“曩”,今通作“曩”。⑥今瑞丽江。 ⑦木邦于明初为府,永乐二年六月改为军民宣慰使司(《太宗实录》卷29),治今缅甸兴威(宣慰),与麓川平缅为二处。钱古训《百夷传》记其事说:“适遇百夷其部下酋长曰刀干孟者叛其国。”《太祖实录》卷亦说:“适其部酋刀干孟叛。”卷说:“麓川平缅宣慰使司刀干孟叛,逐其宣慰使思伦发。”则刀干孟乃麓川平缅酋长,非木邦酋长可知,此文所记与史异。 ⑧事在洪武二十九年。 ⑨即今高黎贡山。 ⑩《太祖实录》卷及《明史云南土司传》作“忽都”。 [11]明初称其时以前来云南的汉人为“旧汉人”。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6《金齿军民指挥使司·风俗》说:“旧汉人有姓氏。世传诸葛武侯引蜀兵平永昌郡,尝留守其地。今诸葛营所居者,皆此类也。言语、服食、衣冠、礼仪悉效中土制度,惟妇人妆饰与云南人同。”万历《云南通志》卷二《永昌军民府·古迹》引曹遇《诸葛营诗》:“孟获生擒雍平,永昌南下一屯营,人也解前朝事,立向斜阳说孔明。”虽然旧《志》以为他们是诸葛亮遗兵之后,不足据,但这些旧汉人于明代已融于人之中了。惟本《书》所说的是“腾冲旧汉人”,不知是否如永昌之旧汉人,抑或即今户、腊撒之汉人。户、腊撒汉人,解放前被歧视称为“小汉人”,解放后自称“大汉人”,其方言、服饰、习俗与该地区汉族有别。青年妇女头裹黑色外接彩带的多层大包头,直径约50—60公分;身著边镶彩条的黑色或蓝色宽大衣裤;善唱山歌,即席赋辞,音声嘹亮动人,与该地区少数民族妇女亦不同。 [12]《太祖实录》卷说:“(洪武三十年九月)戊辰,麓川平缅宣慰使司刀干孟叛,逐其宣慰使思伦发。初,平缅俗不好佛,有僧至自云南,善为因果报应之说,思伦发甚信之。又有金齿戍卒逃入其境,能为火炮、火铳,思伦发喜其有艺能,俾系金带,与僧位诸部落上。刀干孟恶之,遂与其属叛,率其众寇腾冲。思伦发畏其势盛,率其家走云南。西平侯沐春遣送京师。”又说:“(十一月)癸酉,思伦发至京师。上闵之,命西平侯沐春为征虏前将军,左军都督何福为左将军,徐凯为右将军,率云南、四川诸卫兵,往讨刀干孟。”同卷又说:“(十二月)乙巳,遣思伦发还云南。敕谕之曰:`古语有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今尔思伦发长有平缅一方,而与民心好恶不同,故为下人之所不容,而归于我。……然是非不可不明。天讨不可不正,己遣将问罪刀干孟,故命尔还旧邦,……又敕西平侯沐春曰:`思伦发穷而归我,当以兵送还其土。若至云南,令且止怒江,遣人往谕刀干孟,毋为不臣,必归而主。如其不从,则声其罪以讨之。”亦略见《明史·云南土司传》。 [13]《太祖实录》卷说:“是时刀干孟既逐思伦发,惧朝廷致讨,乃先遣人至西平侯沐春所,请入贡。言先尝遣人致方物,乞授土官职事,为大甸刀的弄所劫,由是弗克上闻,愿为奏之。春许之。”同书卷说:“(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庚子,西平侯沐春奏,麓川刀干孟请入贡。且言,刀干孟叛;逐其酋长思伦发,恐朝廷声罪致讨,故来归款。而思伦发所部忽都亦据守腾冲、怒江及景东迤外威远等处,俱已向化归朝。刀干孟惧为所攻,故欲假朝廷之威,以拒忽都。其言入贡,恐未可遽信。……上遣人谕沐春曰:‘远夷诡诈诚有之,然姑从所请,以伺其变。其忽都所守诸部,尔可从宜抚谕。若刀干孟之虚诈,当审度其宜而处之,毋自失事机。’”《明史·云南土司传》亦据此成文。 诏命三司①议。按察司以为毋勤兵远略,请弃之;布政司请待其敝而乘之;都司以为彼既受命为宣慰,穷而不恤则无恩,乱而不治则无威,当为拔②出,然后以兵纳之。朝廷是都司议,令金齿卫遣入谕诸夷,毋遏思伦法;且命虎都沙谨守腾冲府待援。於是思伦法来归,刀干孟遣其属刀名孟攻腾冲益急。四月,我师至金齿,欲遥为声援,待追内地兵至,至冬大举。虎都沙告急,日再至。西平侯曰:“夷人恃炎瘴,度汉兵不能救,故并力攻之。若潜师远袭,出其不意,亦一奇也。”乃命何福、瞿能率兵赴之。至腾冲,召虎都沙议计。沙曰:“夷兵在南甸③者及五万,迫芒干(寨名)而营者,皆悉刺④也,其酋长刀名孟殿其尾。若分兵牵制芒干悉刺,使不得归援,直以精兵击其尾,则刀名孟可禽。其众不战而自溃矣。”夜四鼓,军土蓐食⑤。昧爽,薄其营。夷人诛茆以茇⑥,我兵纵火焚之,夷兵溃,追及刀名孟,斩之。留数日,夷不出,乃还。秋,以西平侯春为征虏前将军,都督福副之,讨木邦叛酋刀干孟。命下,西平侯卒。何福以兵进,与刀干孟战于麓川,禽之。纳思伦法以归⑦。 ①明废元行省制,地方上实行民政、司法、军事三权分立:承宣布政使司管民政,按察使司管司法,都指挥使司管军事,合称三司。这三司是平行的。不相隶属,协同管理地方,而权集于中央。 ②”拔”疑“援”之误。 ③南甸,今梁河县。明初为南甸府,永乐十二年为南甸州,正统八年升为南甸直抚司。 ④李思聪《百夷传》:“正军谓之昔剌,犹中国言壮士也。”钱古训《百夷传》说:“择其壮者为正军,呼为锡剌。”程本立《黔灵昭靖王庙记》说:“寇之勇而力者日昔刺。亦殊死战。”《明史·沐英传》误作“昔刺亦者,寇枭将也,殊死斗”。不仅将“昔刺”与“亦”连读,而且将“昔刺亦”作人名,误甚。“悉刺”、“昔刺”、“锡刺”,译字不同。 ⑤“蓐食”,厚食。义为饱饱地吃。 ⑥“茆”,通“茅”。”茇”,草舍。 ⑦《太祖实录》卷:“(洪武三十一年五月丁未朔),西平侯沐春进兵击平缅。先以兵送思伦发于金齿,使人谕刀干孟,不从,乃遣左军都督何福、瞿能等,将兵五千往讨之。福等逾高良公山,直捣南甸,大破之,杀其酋刀名孟,斩获甚众。回兵击景罕寨,寨乘高据险,坚守不下。官军粮械俱尽,贼势益盛。福使告急于春,春率五百骑往救之。乘夜至怒江,诘旦径渡,令骑驰躏寨下,扬尘以惊之。贼乘高望见尘起蔽天,不意大军卒至,惊惧,遂率众降。春乘胜复击崆峒寨,贼夜溃走。刀干孟乃遣人乞降。事闻,朝廷以其诞诈,复授春征虏前将军,令俟变以讨之。春后病卒,刀干孟竟不降。乃命都督何福往讨,擒刀干孟以归,思伦发始得还平缅。逾年卒。”其事亦见《明史·云南土司传》二。《明史·何福传》说:“是时,太祖已崩,惠帝初即位,拜福征虏将军。福遂破擒刀干孟,降其众七万,分兵徇下诸寨,麓川地悉定。建文元年还京师,论功进都督同知。” 三十二年,以黔灵王①次子晟袭侯爵,来莅是邦②。思伦法既复,日益凋弊。各处土酋闻今天子③即位,各欲致琛献币,自远而朝。乃立孟养、木邦皆为宣慰使司,孟定、孟琏各处皆为府,其下者则为州,又其下则为长官司④。锡以符节,使其子孙世有其土,毋相侵伐⑤。 ①沐英“追封黔灵王”。 ②《明史》卷《功臣世表·西平侯沐英》载:“黔国公晟,洪武三十一年袭侯。”又卷《沐晟传》说:“建文元年嗣侯。比就镇。”建文元年当洪武三十二年,与本文合。《太宗实录》卷11说:“(洪武三十五年八月)甲子,命西平侯沐晟镇守云南,云南都司属卫听其节制。”盖成祖即位后,或是“以岷王与西平侯沐晟交恶”,故重申此令。 ③成祖朱棣。 ④王直(—)《定远忠敬王庙碑》说:“先是诸夷逐麓川宣慰,而分据其地。乃请发兵讨定焉,正其封域而疆理之,置木邦、孟养、孟定三府,镇沅、威远二州,干崖、潞江、湾甸、大侯、者乐五长官司,征其贡赋有常数。又置腾冲千户所于潞江之西以临之。而诸夷莫敢不服。”其具体建置时间,《太宗实录》卷15说:“(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丙辰),设云南孟养、木邦、孟定三府,威远、镇沅二州。”《明史·地理志》:“孟定御夷府,洪武十五年三月为府。”盖后为麓川所占,至是复置。《太宗实录》卷16说:“(永乐元年春正月乙未),设者乐甸、大侯、干崖、湾甸、潞江五长官司,隶云南都司。时西平侯沐晟言,其地旧属麓川平缅,而地广人稠,宜设长官司治之。故有是命。”又卷32说:“(永乐二年六月癸酉),改木邦、孟养二府为军民宣慰使司。”又卷53说:“(永乐四年夏四月戊寅),设孟琏长官司。……隶云南都司。命刀派送为长官,赐冠带印章。”是孟琏为长官司,隶都司,未尝设府。本文言及孟琏为府,或因其地原属孟定,连带及之。 ⑤《太宗实录》卷31说:“(永乐二年冬十月庚午),制信符及金字红牌颁给云南木邦、八百大甸、麓川平缅、缅甸、车里、老挝六宣慰使司,干崖、大侯、里马、茶山四长官司,潞江安抚司及孟艮、孟定、湾甸、镇康等府、州土官。其制,铜铸信符五面,内阴文者一面,上有文行忠信四字,与四面合;及编某字一号至一百号批文勘合底簿,其字号如车里以车字为号,缅甸以缅字为号。阴文信符勘合俱付上土官,底簿付云南布政司,其阳文信符四面及批文百道藏之内府。凡朝廷遣使,则赍阳文信符及批文各一,至布政司比同底簿,方遣人送使者以往;土官比同阴文信符及勘合,即如命奉行。信符之发,一次以文字号,二次以行字号,周而复始。又置红牌镂金字敕书谕之,其文曰:敕某处土官某,尔能守皇考太祖高皇帝号令,未尝有违。自朕即位以来,恭修职贡,礼意良勤。朕以远人慕义,尤在抚绥,虑恐大小官员军民,假朝廷差使,为民扰害需索,致尔不宁,特命礼部铸造印符付尔。凡有调发及当办诸事,须凭信符乃行。如越次及比字号不同,或有信符而无批文,有批文而无信符者,即是诈伪,许擒之赴京,治以死罪。又编勘合一百道付尔,勘合底簿一扇付布政司。尔之境土,凡有军民疾苦及奉信符办过事务、进贡方物之类,俱于勘合内填写,遣人赍至布政司比号写底簿,布政司、都司遣官同赍所填勘合奏闻。若边境声息及土人词讼,从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会同计议行之。其事已行,及尔承行缘由,并填写勘合奏闻。如总兵官镇守遇有前事,总兵官亦会三司计议,仍用都司或布政司印信文书写总兵官处分之语,方许奉行,亦填写勘合具奏。若朝廷命总兵官挂将军印征讨,调遣尔处军马,不待三司行移,但凭总兵官印信文移,即时发遣,亦填写勘合,遣人奏闻。填写勘合或字画错误明白圈注以本司印信盖铃,凡所收底簿及勘合用之将尽,具奏再颁。或总兵官、都司、布政司等官新除,官到任及遇时节,不许赍礼物相庆。今以此敕刊置金字红牌,悬尔治所,永久遵守。仍以纸写一道付尔,或有贪婪无藉凌害尔者,不待填写勘合,正具本遣人赍此敕,不经总兵官及三司,径赴京陈奏,将犯者治以重罪。用此关防,正为抚安尔众,尔当安分循理,谨遵号令,和睦分尔邻境,益坚事上之心,则尔子子孙孙世保境土,及尔境内之民永享太平,其恪遵朕训毋怠毋忽。” 永乐四年,缅甸宣慰使那罗塔①令其酋边住,来献孟养土贡银七百五十两。盖已杀孟养宣慰刀木旦,并其地,来修贡也。初,刀木旦为思伦法陶孟,以女妻之,生子三朋。及思伦法为昭,王也。以他女为昭曩。刀木旦蓄怒未泄,尝率兵攻破金齿,又欲并吞戛里。值内官杨瑄、给事中周让招谕古刺②,往其处。刀木旦说以招戛里,遣人为之导,乃扬言于戛里曰:“将招尔属孟养,必尽杀之。”戛里怒,杀其导,刀木③旦遂执词以伐之。戛里以妻子质于缅,乞援,缅人据南的美④江,断孟养所来路,运饷不通,刀木旦卒饥,欲解去,戛里出击之,缅人要于路,刀木旦全军陷殁。孟养立其子思鸾法,与其弟分赀不平,其弟亡入缅,缅人发兵送之,杀思鸾法,虏其亲属以归。未几,又杀其弟,以酋长西得抚其众,觊得其地⑤。 ①《明史·云南土司传》三说:“缅甸,古朱波地。……(洪武)二十七年,置缅中宣慰使司,以土酋卜剌浪为使。……永乐元年,缅酋那罗塔遣使入贡,因言:`缅虽遐裔,愿臣属中国,而道经木邦、孟养,多阻遏。乞命以职,赐冠服、印章,庶免欺陵。诏设缅甸宣慰使司,以那罗塔为宣慰使,遣内臣张勤往赐冠带、印章。于是缅有二宣慰使,皆入贡不绝。”又说:“初,卜剌浪分其地,使长子那罗塔管大甸,次子马者速管小甸。卜剌浪死,那罗塔尽收其弟土地人民。已而,其弟复入小甸,遣人来朝,且诉其情。敕谕那罗塔兄弟和好如初,毋干天讨。”该《传》又说:“宣德元年,遣使往谕云南土官,赐缅甸锦绮。二年,以莽得剌为宣慰使。初,缅甸宣慰使新加斯与木邦仇杀而死。子弟溃散。缅共推莽得剌权袭,许之。自是来贡者只署缅甸,而甸中之称不见。”哈威《缅甸史》(姚楠译注,陈炎校订,7,商务印书馆)“缅王明吉斯伐修寄(Minkyiswasawke,—1),译者按:即《明史》所志之卜刺浪。”(页)《注》云:“明恭王(Minhkaung,1—22年)应即为《明史》所志之那罗塔。”(页)“梯诃都(Thihathu,2—6年)疑即《明史·缅甸土司传》之新加斯。”(页)“孟养他忉(—40年)应即《明史·缅甸土司传》所志之莽得剌。”(页)惟哈威《缅甸史》说:“明吉王…年七十而薨。宫中曾一度相互残杀,王位卒由其幼子承袭。”是明恭王乃明吉王的幼子,而《明史》所载,那罗塔乃卜剌浪之长子,未详哈威及《注》所述确否? ②此事《明史》不载,详见《太宗实录》。《太宗实录》卷22说:“(永乐元年八月)庚午,遣内官杨宣等赍敕抚谕麓川、车里、八百、老挝、古刺、诏闽、特冷、冬乌、孟定、孟养、木邦等处土官。仍命西平侯沐晟遣人谐行。”卷33说:“(永乐二年八月已丑),至是瑄等道经八百大甸,为土官刀招散所阻,弗克进。”及至永乐三年秋七月“壬子,车里宣慰使刀暹答遣头目揽线思奏,请举兵攻八百大甸宣慰使刀招散。上……又遣使谕八百大甸军民宣慰使刀招散等曰:‘其车里、者乃、老挝、木邦、孟养诸宣慰使及孟定、威远等府州官皆敬恭朝命,无所违礼,惟尔年幼无知,惑于小人孟乃朋、孟允公等教诱,起祸生衅,闻使臣至境,拒却不纳。朕遣颁诏往谕古剌等处,尔阻遏之。尔之罪愆,不可悉数,廷臣咸请兴师问罪。朕念八百之人岂皆为恶,兵戈所至,必及无辜,故有所不忍。兹特遣司宾田茂、推官林祯赍敕,同车里差去人往谕,尔能改过自新,即将奸邪之人擒送至京,庶几境土可保,人民获安。其或昏迷不悛,发兵讨罪,拿戮不贷。’遂敕西平侯沐晟谕以车里请往八百之故,且言已遣使往谕八百,令改过自新,尔宜严兵以待。彼果悔罪输诚,即止兵勿进。其以马军六百、步军一千四百随内官杨安、郭斌。又虑老挝乘车里空虚,或发兵掩袭其后,或与八百为援,可选的当头目率兵一万五千往备。”(《太宗实录》卷49)同年十二月“戊辰,镇守云南西平侯沐晟奏:‘奉命率师及车里诸宣慰兵,至八百境内,破其猛利石厓及者答二寨,又至整线寨;木邦兵破其江下等十余寨。八百恐惧,遣人诣军门陈词伏罪。’……遂敕遣谕车里、木邦宣慰使刀暹答、罕的法,波勒、马艮等土官麻哈旦麻剌吒等曰:“曩者八百不恭朝命,尔等请举兵诛,嘉尔忠诚,已从所请。今得西平侯奏言,八百已伏罪纳款。夫自有罪能悔,宜赦宥之。敕至,尔等悉止兵勿进。又敕西平侯沐晟等班师。”(《太宗实录》卷39)据《太宗实录》卷54说:“(永乐四年五月丁巳),云南腾冲守御千户所千户孟景贤等自大古剌还。……初,中官杨瑄与景贤等赍诏往抚谕之,(土酋)泼的那浪见使者不下拜,……遂徙置瑄等于南难河,拘留不遣,瑄等亦不屈。其左右言于泼的那浪……。泼的那浪惧,乃礼谢使者。先遣头目选马撒等随景贤朝贡,继遣头目独金不剌等护送瑄等还,且贡方物谢过,而大古刺所属诸酋长皆遣使朝贡。”则杨瑄此次出使,自永乐元年八月至永乐四年五月,历时两年零九个月,先后被阻于八百大甸及大古刺。其间,明王朝又派给事中周让往使。《太宗实录》卷45说:“(永乐三年八月)辛未,遣给事中周让等往赐孟养军民宣慰司及大古剌、小古剌、底马撒、茶山、孟伦等处土官文绮采帛等物。”同书卷54又说:“(永乐四年五月甲辰),给事中周让等使小古剌等处还,赐钞、文绮袭衣。”则周让这次出使是从缅甸北部孟养起至缅甸南部小古刺、底马撒等地而还,与杨瑄自车里、老挝、八百至古剌等地,所循方向似相反而互补。途中是否相会,未见记载。但是大古剌等处遣使朝贡后,周让又再度出使。《太宗实录》卷55又说:“(永乐四年六月)壬午,大古刺等处土酋泼的那浪所遣使臣选马撒等言,其邻境有七,曰大古剌、小古剌、底马撒、茶山、底板、孟伦、八家塔,皆在西南极边,自昔不通中国。今天朝遣官宣布恩命,人民皆愿内属,乞设官统理,仍招谕旁近未附之民。从之。以大古剌、底马撒二处地广,各置宣慰使司;小古剌、茶山、底板、孟伦、八家塔各置长官司。以泼的那浪为大古剌宣慰使,腊罔帕为底马撒宣慰使,拜张、早张、看伽立昧、刀罕替、刀轻罕为小古剌等长官使长官,俱给诰、印、敕、符、金字红牌。遣给事中周让等赍敕往赐之,仍各赐钞、币有差。”《明史·地理志》七说:“大古刺军民宣慰使司,在孟养西南。亦曰摆古,滨南海,与暹罗邻。底马撒军民宣慰使司,在大古剌东南。小古剌长官司、茶山长官司、度板长官司、孟伦长官司、八家塔长官司皆在西南极边,俱永乐四年六月置。”即指此事。大古剌、底马撒、小古刺相当于《新唐书·骠国传》中之大昆仑王国、昆仑小王及小昆仑部之方位,其地在今勃固、田那西林及勃生。参见拙作(《交广印度两道考辨误》第五节《弥臣国与昆仑国》(《民族学报》1年第1期)。 ③原本误”水”,今据滇钞本及《明史》、《明实录》正。 ④原本作“”,字书无此字。今据滇钞本作”美”,未知确否。 ⑤详见下注。 天子命行人臣洪往谕之,且索刀木旦子孙,复立孟养。那罗塔以刀木旦首乱为辞,曰:“彼加兵于我,不得已而应之。其子若孙没于乱兵,故令西得暂抚,□□□甚安,不敢废职贡也。”行人诘之曰:“戛里本夷,非缅属类,何云加兵于尔?□□□皆归职方,惟戛里深窜不出,王法所当讨也。孟养执言讨之,非首乱也。尔不率职而党恶,其罪均也,况杀邻境之宣慰乎?尔欲朝廷置而弗问,设尔之酋杀他酋以并其地,尔可弗问乎?行人之来,欲以兴灭继绝者,岂专为孟养哉?尔后日子孙亦蒙福利也。尔不奉诏。则使还而兵至矣!”①那罗塔大惧,遣陶孟洛霞赍缅书、方物赴阙待罪②。虽未即讨,而缅人知所自戢,远方小夷皆得以自安也。 ①《太宗实录》卷57说:“(永乐四年闰七月己巳),云南守臣言:‘缅甸军民宣慰使司宣慰使那罗塔擅加兵孟养,杀其宣慰使刀木旦父子,请发兵讨之。’遂遣行人司行人张洪赍敕谕曰:‘人君受命主宰天下,必明法令,一人心,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各安其生。朕自即位以来,万姓归心,四夷听命。尔那罗塔亦克敬顺天道,恪修朝贡,抚安一方之人,朕甚嘉之。今闻与孟养构兵,杀其宣慰使刀木旦父子,虏掠其人,侵其土地,何异往者之心也?揆之国法,其可容乎?边臣请发兵问罪。朕虑大军之行,滥及无辜。今特遣行人张洪赍敕谕尔,其速易心改虑,勉修善道,还所侵地及虏掠之人。自今奉法循理,各守疆场,以安其民,庶几可免前罪。如复冥行不悛,天讨必加,悔将无及。’”《明史·土司传》三《孟养》说:“(永乐)四年,孟养与戛里相仇杀,缅甸宣慰那罗塔乘衅劫之,杀刀木旦及其子思栾法,而据其地。事闻,诏行人张洪等赍敕谕责缅。那罗塔惧,仍归其境土。” ②《太宗实录》卷49说:“(永乐五年夏四月丙戌),缅甸土官那罗塔等遣其属陶孟洛霞等诣阙,贡方物,谢罪。先是孟养宣慰使刀木旦与戛里相仇杀。而那罗塔乘衅发兵劫之,杀刀木旦及其子思栾发,掠其人口、牛马,遂据其地。事闻,诏行人张洪等赍敕谕责之。那罗塔惧,遂归其境土及其所掠,遣人诣阙。请上谕礼部臣曰:‘蛮夷既服辜,即释不问。一体给以信符,令三年一朝贡。’”亦略见《明史·土司传》三《缅甸》。 张行人曰:蛮俗虽陋,而土酋世袭之制,有古封建之余风,植遗腹朝委裘之遗意①。酋死无子,而妻得以临其民;妻死,女得以继其母。虽凶犷如狞兽,莫不稽颡伏地,惟其命而生死之。故蒙、段二姓据有其地,各四五百年,与中国汉、唐家相终姓②。非有商、周之德以永年,特以土有常尊,人有定主,不可以移易也。元世祖虽灭段氏,叛乱者四十余年,得赛典赤敷治,夷始贴服。末年,其俗殷富,墟落这间牛马成群;仕宦者莝稻秣驹,割鲜饲犬;滇池之鱼,人饫不食,取以粪田,物盛则衰,理固然也。及天兵压境③,答里麻来拒,将骄卒惰;故长驱以定其地,吏民安④堵不动。苟不猖獗叛乱,虽至今其犹存。乃去安即危,出入生死者,岂非乐其故,而重改更也耶?然而力分于众建,故难合而易散。又各处卫所据腹⑤饶地,扼吭以制其死命,是以从化之速也。加以黔灵之严重,故强梗者相次而詟服。独百夷全据三十六部⑥,并力以自雄。入寇景东,攻陷金齿,于是有定边之举,欲以抗衡中国。黔灵从容应之,歼其渠帅,夷始夺气,无复东略。乃移毒于下,骄主疲民,兵法所忌,况思伦法惟妇言是用,不亡得乎?朝廷因势而分之,非不幸也。缅人不以思伦法为鉴,复肆贪并。天子命行人一出,而大义凛然,不待行师而已屈服其心矣。辞乎!辞乎!其义之先声乎!故君子不可不慎也。 ①《汉书》卷48《贾谊列传·疏》说:“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遗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当时大治,后世称圣。”服虔曰:“言天下安,虽赤子、遗腹在位,犹不为也。” ②“汉、唐”当为”唐、宋”之误。据《南诏野史》(明钞本),南诏自唐永徽四年至天复二年(—年),共二百五十年;大理国自晋天福二年至宋宝祐元年(—3年)共三百十五年,均不合“各四、五百年”之数。本书盖漫言之。③原本脱“境”字,以意增。 ④原本作“按”,兹从滇钞本。 ⑤原本作“服”,以意正。 ⑥“部”当为”路”之误。《云南机务钞黄》载洪武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敕谕》:“遣官间问云南老人,皆说死可伐地方三十六路。”(亦见《太祖实录》卷)可证。 附录 一四库馆臣按语 谨按:《南夷书》一卷,明张洪撰。考明永乐四年,缅甸宣慰那罗塔刦杀孟养宣慰使刀木旦①及思栾发,而据其地。洪时为行人,奉诏赍敕宣谕,因撰是书。所载皆洪武初至永乐 四年平云南各土司事,略而不详。其于云南郡建置始末,如南诏为蒙氏改鄯阐府②,历郑、赵、杨三氏,始至大理段氏,而书中遗之;孟养、麓川各有土司,而叙次未详。唯载梁王拒守及杨苴乘隙诸事,史所未载。澜沧之作兰沧③,思栾之作思鸾发④,与史互异,亦足资考证之一二也⑤。洪字宗海,常熟人。洪熙初召入翰林,官修撰。 纂修官程晋芳存目 ①《总目提要》误将“木旦”二字全为“查”字。②此语不确。南诏为国名,鄯阐为城名,其地在今昆明市。《滇载记》说:”(南诏)都曰苴咩,别都曰鄯阐,皆中国降人为之经画也。”段氏始建鄯阐府,为八府之一。③《总目提要》误改为“澜沧江作兰沧江”,盖本书只言“兰沧卫”,未涉及“兰沧江”。《太祖实录》卷说:“(洪武二十八年九月壬子),调云南中卫于北胜州,置澜沧卫。”明初澜沧卫治在今永胜县,与澜沧江无涉。④本文当作“思栾发作思鸾法”。“之”乃“发”之误,末“发”字当作“法”。盖《明实录》、《明史》作“思鸾发”,本书作“思鸾法”。《总目提要》作“思栾发作思鸾发”,末“发”字虽涉上音近而误,前“发”字尚堪作证。⑤《总目提要》将此句改作“盖亦译语对音之故也”。 二滇钞本后记 南夷书,明张洪著,淛抚三宝呈进、四库馆存目发还天一阁范氏钞本。有翰林院印一方,浙抚送书印一方,纪文达题笺一纸,纪晓岚、陆耳山二人恭阅印一方,翁同和书面题字并翁氏藏书印六方①。此书因索值奇昂,关于吾滇考据事,而又不忍舍去。措辞借阅后还价,限一日归还。故作半日忙将全书抄下,拟将来寄归云南省图书馆,作研究明代吾滇掌故之珍贵史料云耳。已卯②春,腾冲张荣庭木欣记于戛里胡同寓所。 ①此本今藏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室,为翁斌孙赠书。该书每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字。封面书签空白,靠书脑题“南夷书常熟张洪著”一行,为翁同和所书;中下方有“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浙江巡/抚三宝送到范懋柱家藏/南夷书一部/计一本”四行正楷长方印。扉页内侧书签题“南夷书”,下有“臣昀臣锡熊恭阅”长方印;有“总办处阅定/拟存目”三行戳记;骑签有“翁同和校定经籍之印”。首页正上方盖有“翰林院印”汉、满文大印一方;内侧有“曾在赵元口家”长印,“虞山翁同和印”方印。书尾有“均斋秘芨”矩形印、“救虎阁主”方印、“紫芝白龟之室”白文方印。 ②己卯为年。 三张洪《平缅录》① 永乐四年闰七月十二日,命持节八缅,谕那罗塔。即日就道,九月至金齿,整点护敕。官军从行者举家痛哭,谓去必死。洪示以间暇,不急于行。哭送者不知其期,稍懈,乃疾启门驰出,抵诸葛营而止。哭者不得相送,行者免于趋事。时内官云仙在麓川,病,遣军迎于道,见者皆泣。及至麓川,云仙要洪入,臭秽不可坐,以军士营居,无厕,且天气郁蒸故也。行次贡章,即缅之江头城。缅既并孟养地,复遣陶孟东如聚兵于此,以防中国之救。洪佯为不知,遣人斥曰:“我使日本,其王来迎,舟揖遍海。尔曾不满二三万人来接,是轻我也,速备船送。尔本小夷,吾不汝尤。既入舟,召通事询缅事情及前使得失。通事对曰:“缅酋甚倨,闻朝使来,则创草楼北面以迎之。使臣入城,闭其从人于外,使之徒行,延登草楼,缅人则南面与之语,率以为常。前使者姑容之。且其风土甚恶,至之夕,病者居半,明日尽病,三日后死者相继,十无一还。公宜处之。” 洪入其境,遣通事谕缅人撤去北面之楼,且告以中国之礼,为官者出,行者皆避路,否则箠之,且告缅民避路。乃选敢死士二十,外佩刀执杖。将入城,洪立马城下,叱缅人癖门。不听,遂箠之,排其门而入,至宣慰庭。缅人列象百余,夹道而立,以鼻勾绾,请使臣下马。即令拔刀斫象鼻,象始开,驰至其楼。奉敕书,南面呼宣慰以下北面听受。毕,使者西向坐,数其失礼并擅杀邻近土司罪。那罗塔不能答,但云:“请就馆,明日回复”。 既退,缅人杀牲以供具,悉麾出,令命②易生牢来。旧闻夷缅间有木,曰金刚纂,状如棕榈而无叶。剉以渍水,暴牛羊渴甚而饮之,食其肉必死。继馈生牢,必俟三五日无毒,然后烹宰。扫除营内,无容秽恶,于营外百步许为厕,满则实之以土,更为别厕。三日,军无病,心始安。彼常以瘴病怖我,故前使畏死,求亟还,莫敢与之校。以洪观之,瘴疠虽有,亦当调摄。食肉不许太过,饮酒不至于醉,居处无臭秽,衣食以渐增减;丑献游行必防其毒。缅人常蓄淫妇,诱我士卒,犯之必死,谓之人瘴。洪朝夕诲之曰:“汝等来时,父母妻子哭送,拜祷神明,望若生还。今以人瘴而毙,妻必他适,父母何归?”众皆感泣,不敢近人瘴。或有病疟,洪以平胃加柴胡治之,多愈。去时马、步七十人,归时六十九人。惟一人朱观音保殁于彼,命从者收骨殓随身行李还其家。缅人以军无死伤,称为神明。使事毕,还至腾冲。既脱瘴病,安养军士数日,夷人馈牛、酒,悉以享士,死者亦与祭。振旅入金齿,欢声动地,人得生全,皆以为异事云。 ——录自《滇系·典故》八 ①《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存目》八著录张洪《使规》一卷。《提要》云:“末为《使缅附录》。纪当日往返情形。并载所与缅酋书六篇。”《使规》一书未见,惟据《提要》所说《使缅附录》的内容,几与《平缅录》同,《平缅录》似应作《使缅录》,始与所记内容差合。容俟异日能获阅《使规》一书以决之,井应转录《与缅酋书》六篇。今暂从《滇系》作《平缅录》。 ②“令命”二字当衍其一。 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3期。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gaoliangjianga.com/gljtx/6439.html
- 上一篇文章: 每天学一味中药,白芨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