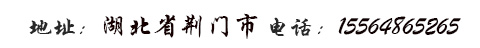红颜劫一位乳腺癌患者的自述
|
33岁的歌手姚贝娜因乳腺癌复发病逝,令人扼腕叹息。 1月16日下午5时左右,这位勇敢坚强、热爱唱歌和生命的女孩终未能战胜病魔,病逝于深圳,年仅33岁,姚贝娜昏迷前签了眼角膜捐献书。 在乳腺癌这条路上,走过了一个又一个年轻女性的生命。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讲师于娟,就是其中之一,年12月确诊患乳腺癌被判只有一年半载的生命,年4月19日于娟病逝,同样年仅33岁。 她生前写的“活着就是王道”的博客,辑成《此生未完成》一书出版。作为癌症病人,她从容淡然,从不哀伤;她已辞世,却与身后的世界同在。以下文字摘自《此生未完成》—— 于娟|文 我是入院很久才听说义乳这个词。一般的乳腺癌患者,都是45岁以上发病,若是运气好发现得早,没有远端转移,一般会接受切除手术。中国很多病人当被问及“是否要保乳”,通常都是底气十足地说“保命!保乳有啥用?”所以,化疗病房通常住的都是只剩下一只乳房的老女人们。我是患者里年纪最轻但是运气最差的一个,发现时已然专业扩散得厉害,所以没有可以动手术的资格,所以也是唯一不需要义乳的人。
现在想来,乳房可能是女人身上最为没用的器官,所以义乳不需要义肢那般实现什么功能,只需要做个体积出来,穿上衣服之后具有观赏价值就可以了。义乳卖得很贵,差不多多一只,附带在一只特制的胸罩里。很多上年纪的阿姨虽然爱漂亮,但是更爱钞票,所以都觉得多买个布袋没有太大意思,于是八仙过海一般各自动手做义乳。
南翔李阿姨癌龄比我们长,又爱漂亮,最先开始做义乳。她传给大家的失败经验是,不能用棉花布头做小袋子塞在文胸里。因为“那芯子轻”。据她亲身介绍,一次戴着自做的棉花义乳去即公交车,下车后发现大家都在看她,目光怪异。阿姨低头一看,原来伸手在车上拉吊环的时候,那棉花团被挤来挤去,跑到了肩膀下方锁骨的地方。乳房长在肩膀上的女人比没有乳房的女人更能吸引众人目光……
舟山庄阿姨非常有趣。劳动妇女天生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她一开始就没有用棉花,而是选择了下垂感极强的绿豆。人家用绿豆缝了个沙袋,放置左胸充当义乳。形态很好而且谁也看不出那是假的。庄阿姨为自己的聪明才智省下了多而洋洋得意。房间里数个老太纷纷效仿。然而第四次化疗之后,庄阿姨的大女儿就发现了问题,她觉得妈妈的两只乳房越来越不相称,绿豆义乳明显感觉膨胀肥大。于是小女儿趁妈妈洗澡的时候把绿豆沙袋从胸罩里掏出来拆开,结果让大家捧腹大笑:那绿豆因为体温汗水,发芽了。
庄阿姨一度沮丧,埋头创新,苦苦思索之后决定不再使用豆类做填充物,改用大米。大米倒是不发芽,但是无奈天气转热,大米义乳不过两个星期,开始发霉。
奉贤有个退休甘老师,可能因为受教育程度高一点,对于差不多小学毕业的庄阿姨的举动颇不以为然。她受过教育,认为茶叶对人体好,于是把茶叶晒干了像填枕头那样做茶叶义乳。实践出真理,茶叶的确不会发芽,也不会发霉,也的确有香气。但是乳房比头颅要娇嫩,甘老师花了数个星期做好的义乳,戴了不到半天就气呼呼扔到一旁:茶叶梗叶太硬,开过刀的地方被它刺得难以言表。 我虽没有义乳需求,但也热情澎湃参与义乳创新。或是人格魅力,我在病房到真的有一大票fans,因此我的主意创新很容易被人实践实现。我说“外面不是卖那种水珠按摩胸罩吗?他们是为了让小胸看起来大,我们做大一点是不是就可以让大家看起来从有到无呢?”我的馊主意是:把气球灌水。当年出主意的时候我因为癌细胞骨转移而浑身不能动,黄山的吴阿姨是脑部转移,癌细胞不发作不疼痛的时候和正常人一样,她很是喜欢这个主意,于是实践了一把。出医院去吃饭的时候就用气球装点水放在衣服里。有一天我躺在床上听到走廊一片大笑,吴阿姨捂着肚子弯腰进来“于博士啊,今天电梯太挤了,把我的气球奶奶(她把乳房叫奶奶)给挤破了,我的衣服湿得哟……” 对一个学了十几年经济学的人来说,看到PICC的第一反映是****保险公司。
然而,如果对一个学了十几年经济学,患了半年癌症同时接受了半年化疗的人来说,PICC是就是单腔三向瓣膜式PICC导管,就是一根深入你体内45cm的蓝色塑料管,就是唯一也是最为接近你心脏的体内异物,就是你埋在手臂上肉体里仅仅露出1.5cm的医疗管,无论何时都贴满了3M贴膜。只看胳膊,就感觉是好莱坞生化大片里主人公的胳膊。 化疗会让静脉血管萎缩,但不是所有的化疗药物都有这种副作用,所以不是所有化疗病人都需要穿PICC保护静脉。然而,我却没有选择。因为我的化疗方案是素以“病重下猛药”出名的J主任亲自定的。药物的毒性巨大,虽对癌细胞可以有效控制,但对身体各方面机能的伤害也是不容忽视。我必须要装一根管子,从手臂的静脉植入身体,一段留置在体外,另一端要伸到心脏的附近。 化疗方案定下来之后,便有一个接一个的护士鱼贯而入,一个接一个要求看我胳膊。而后三五成群窃窃私语地离开。一时间搞得当时只能横躺的我心情极具忐忑。 那帮护士在讨论,谁有本事给我穿PICC。穿进去,要付钱。穿不进去,因为管子是一次性的,开过包了,所以打开了即便穿不到你身体,也是要照样付费。医院规定,就像是你到了一个馆子吃饭,人家给你上了菜,死活不管能不能吃,你都要付钱。 人生中很多经历都有着相似之处。突然之间你会遇到一件颇为让你紧张的事情,而在此之间没有任何常识。在这时候,你所做的,必须是采集相关信息和他人经验,火速做出适合自己的决断。事后成为化疗的“老运动员”之后,我才医院可以在B超下引导穿导管的…… 不过我的情况是必然要弄个管子进入身体,如果穿不进去,那么我就要动手术一样,让人家从锁骨的地方嘎开一刀,埋一根其他名字的管子替代常用的PICC。光头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的的心理素质向来为我暗自敬仰,但和医生护士谈过话回来说服我装PICC的时候也不禁动容。于是我一颗心被一只无形的长满毛的猩猩爪子,凌空提了起来。 因为我是J主任亲自从20楼转下来的病人,护士长似乎表示出格外关心,查看好我的血管之后,说,我来亲自给你穿PICC吧。 光头(于娟丈夫)感恩戴德地狂点头,就差给人家小姑娘作揖了。因为光头的脑袋是格式化的,护士长肯定是技术最高明的一个…… 为了缓解我的紧张心情,光头(于娟丈夫)开了随身电脑,用幻灯片的形式让我侧头看土豆(于娟儿子)的新照片,背景音乐很有心思的用了《春江花月夜》。这个RJ医院22楼乳腺中心是新建的,护士队伍属于是卤水拼盘,良莠不齐。因此我在被穿PICC的过程中还要作为护理课教学实验道具:那个和我同龄的护士长带着一堆小护士把我的床团团围住,把我的右手臂用碘伏像洗澡一样吐了个黄登登的,就像是做什么手术。我侧身不敢看,就听着护士长说“这种静脉属于比较好操作的”。话音未落,我的手臂突然一阵剧痛,忍不住回头一看,立马给雷住了,那护士长拿着的针是我前所未见过的粗啊,比当年我献血的巨型针头还要粗得多得多。我不禁“啊”得叫起来,没有想到,那护士长说“哎呀,不行,她的静脉没有想象得好。” 在我在心里暗自骂娘之际,那护士长从我体内拔出了看似给大象或公牛之类注射用的兽医针,一阵稀稀疏疏在我柔弱的小胳膊上按了很久之后,又捡了个地方,毫不留情以农村大妈纳鞋底的工作作派又是一针,我靠,剧痛啊剧痛,最不能忍受的是,我刚想问是否穿成功了,那个护士长甩了一把汗,底气不足地吩咐一个小护士说“去把张男叫来,这个静脉比较难”。若是按照我以前的脾气,早就发飙了。然而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当时是,我皱着眉头把要说的话咬着舌头吞了下去。 事实证明,在医院里,有行政职称的“长”之流的人物,业务实在是差得让人大吃一惊。 结果一个风风火火的张男闯了进来,进门看着我说“你好,我是张男,弓长张,男厕所的男。”我被这自我介绍逗得哈哈大笑,没想到来者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火速移位到原来护士长站的位置,按都没有怎么按我的胳膊,就咵哒一下用那个该死的针戳进了我的身体,我还没有叫出来,她说“搞定!你别看!”。 然后就真的被她那么漫不经心的搞定了。紧接着,把那根管子顺带一根不知道什么质地的金属丝戳到我静脉了,一直捅到他们认为的心脏附近,然后抽出金属丝,把管子留在那里。这个过程是后来男厕所同志将给我听的,我当时只敢盯着那个儿子照片的幻灯片,但屏幕上是我儿子还是老子根本不知道,脑子里一片空白。 等那几只长着翅膀的鸟人,白衣天使飞走之后,我看到自己胳膊下面已经鲜血殷殷。护士长练兵穿失败的地方铁青暴肿,疼痛与喧闹留下的,只是一小段埋入身体露出头的蓝色塑料管子,还有一白色的固定器。
公元年1月7号之后,我成为了PICC人士。
PICC的确有PICC的好处,此后任何静脉注射,我不必再处心积虑挑选哪个护士给我扎针,更不必用心良苦在不得罪人的情况下委婉拒绝哪个学艺不精的护士。哪怕我看到那个令病人闻风丧胆十针九不进的护士托着消毒盘走向我,也能够面不改色心不跳,只要她能对准扎到电话线电线杆,我就不怕她,呵呵,因为那个PICC留置在我体外的橡胶头,有半个指甲大,她十针只要有一针扎到那个橡胶头上,就可以了。最重要的是,无论她怎么乱戳,都是橡胶头而不是我的肉痛。
但是PICC也有PICC的坏处。我穿的位置尤其不好,在肘部,这就意味着我PIC的右胳膊不太能自由活动,不能提重物,不能弯曲折损,不能碰水,甚至不能……自己吃饭和擦屁股。 作为一名因为癌症转移扩散而全身纹丝不能动的晚期患者而言,不能自己吃饭擦屁股这类事情已经太小太小了,我一点都不怕全世界的人知道,我的右胳膊半年没有洗澡过,穿刺点后面的皮肤可以撮泥丸,与此同时,光头(于娟丈夫)帮我擦了半年的屁股。 …… 也许事情来得太过突然,当我知道身患癌症的时候,已然晚期,癌细胞扩展全身躯干骨。以前读武侠小说,看断肠蚀骨腐心之类词并不陌生,但未必真的解意。这一遭癌症晚期骨转移的经历,我突然明白,蚀骨是骨转移,断肠与腐心是化疗体验。 回望此间半年,几经濒死病危,数次徘徊鬼门。其实作为人,并不是死过一次就不怕死了,而是越死越怕死。所谓更怕死,无非是对这个世界的留恋越重而已。在此之前我是个有知识没文化的俗人,除了学校的哲学课本,就只有初中读过基本德国哲学简史的简明本。从来没有考虑过生死,更不要说从哲学上去看待生死。如此折腾半年,差点把我折腾成研究有关人生生死的哲学家。我对朋友说,别看你在JD教哲学,你未必现在有我现在思考的哲学问题多。如果说癌症对人有正面作用,此算其一,因为癌晚期里你很容易活明白。虽然,可能有点晚。
此前我是个极度开朗好友的人,这可能和性格有关,之前总是觉得能见面,谈得来就是场缘分,就是朋友,于是我朋友无数,三教九流各种各样。朋友多自然是好事,但朋友太多也会形体赢累,心力乏苦。许是太年轻,许是愚钝,我总不知道在茫茫人海中甚至在我所结识的所谓朋友中如何去筛选真正的朋友。有一天突如其来的癌症席卷了我的全部,扬尘散土,洗沙留金。我只需静静躺着,闭眼养身,便可以分辨哪些是朋友,哪些是所谓的朋友。这对我来说,是件大幸事。因为我是为了朋友可以付出很多很多的人。癌症一事,让我知道,若仍有后世,谁是我应该付出的人。朋友访我或是不访,都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当他得知我生病消息的第一反应,眼神表情乃至电话语气网络留言里端倪尽出,你会觉得世间很多人情世故是那么的让你淡然一笑。癌症的后遗症,会让当事人内心更加敏感而外在表现愈加愚钝。我想我终于修成了此前羡慕而终不能得的“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此算癌症益处之二。 癌症是我人生的分水岭。别人看来我人生尽毁。也许人生如月,越是圆盈便越是要亏缺。若旁观者,我是够他妈倒霉的。若论家庭,结婚八年,刚添爱子,昵唤阿尔法。儿子牙牙学语。本是计划申请哈佛的访问学者,再去生个女儿,名字叫贝塔。结果贝塔不见,阿尔法也险些成了没娘的孩子。回望自己的老父老母,独生女儿终于事业起步家庭圆满,本以为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不想等来的却是当头敲晕了的一棒,差那么一点点白发人送黑发人。若论事业,好不容易本科硕士博士出国一道道过五关斩六将,工作刚刚一年,风生水起刚刚开始,申请项目无论国际国家省市全部揽入。犹如鹤之羽翼始丰,刚展翅便被命运掐着脖子按在尘地里。命是否保全是悬念,但是至少,这辈子要生活在鸡的脚下。 其实,我很奇怪为什么反而癌症这半年,除却病痛,自己居然如此容易快乐。倒霉与否从来没有想过想过。我并没有太多人生尽毁的失落。因为,只有活着有性命,才能奢谈人生。 而我这多半年,更多在在专心挣扎努力活着,目标如此明确和单一,自然不会太多去想生命的外延。而三十岁之前的努力更多是因为自己有着太多的欲望和执着,从没有只要活着就好的简单。我不是高僧,若不是这病患,自然放不下尘世。这场癌症却让我不得不放下一切。如此一来,索性简单了,索性真的很容易快乐。若天有定数,我过好我的每一天就是。若天不绝我,那么癌症却真是个警钟:我何苦像之前的三十年那样辛勤地做蝂捊。 名利权情,没有一样是不辛苦的,却没有一样可以带去。 (本文选自《此生未完成》,作者于娟) 《红颜劫》 斩断情丝心犹乱 千头万绪仍纠缠 拱手让江山 低眉恋红颜 祸福轮流转 是劫还是缘 天机算不尽 交织悲与欢 古今痴男女 谁能过情关 拱手让江山 低眉恋红颜 祸福轮流转 是劫还是缘 天机算不尽 交织悲与欢 古今痴男女 谁能过情关 谁能过情关 小山重叠金明灭 鬓云欲渡香腮雪 懒起画蛾眉 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 花面交相映 新帖绣罗襦 双双金鹧鸪 新帖绣罗襦 双双金鹧鸪 懒起画蛾眉 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 花面交相映 新帖绣罗襦 双双金鹧鸪 新帖绣罗襦 双双金鹧鸪 双双金鹧鸪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gaoliangjianga.com/gljtx/9602.html
- 上一篇文章: 正能量一个勇敢乐观的乳腺癌幸存者,摄影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