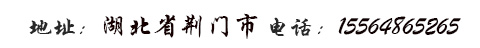临床应用五苓散的经验
|
湖南白癜风医院 http://m.39.net/baidianfeng/a_4322074.html 五苓散是《伤寒论》中的一首著名的方剂,首见于《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太阳病,发汗后,大汗出,胃中干,烦躁不得眠,欲得饮水者,少少与饮之,令胃气和则愈。若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五苓散主之。” 对于五苓散的病机用药,历代医家多有论述。笔者有幸跟随我校伤寒专家傅元谋教授出诊,临床常见傅老以五苓散加减治疗各种疾患,效果甚佳。现就老师临床应用该方的经验体会,结合自己的点滴心得,整理成文,与同道共参。 用方心法病机方面对于五苓散的病机,历代医家众说纷纭。综观各家对其病机的认识,不外三种。 一者,即现行《伤寒论》教材所注,乃太阳病汗后,表邪未解内传膀胱,影响膀胱气化,致使水湿停蓄于内,形成蓄水证。 二者,认为五苓散乃由于汗下之后大伤津液,兼有余津不能四布所致。 三者,还有一派医家另辟蹊径,提出“脾不转输”说。如张隐庵提出:“大汗出而渴者,乃津液之不能上输??盖发汗而渴,津液竭于胃,必藉脾气之转输,而后能四布也。”用五苓散是“取其四散之意,多饮暖水汗出者,助水津之四布”。 傅老认为,三种解释中以第一种解释最符合仲景原意。五苓散由猪苓、茯苓、泽泻、白术、桂枝组成。方中重用泽泻,同时有猪苓、茯苓淡渗利水,白术助脾气转输,桂枝轻用,通阳化气,助膀胱气化,兼以解表。全方具分利、转输、通气的特点。方中药物组成及其剂量分布,均符合蓄水证的病理特点。但临床上后两种情况也较常见,以五苓散治疗亦取效颇佳。 仔细分析三者病机,“气化不行,水津输布不利”乃其共同之处。故在辨证用药时,不必拘泥,只要抓住“气化不利,津液不布’’这病机关键即可。 用药方面在用药方面,傅老认为虽然五苓散的病机关键是‘‘气化不利,津液不布”,但用药时也要分而论之,根据具体情况适当调整各药间的比例。 若属膀胱气化不利,水液不布,蓄于下焦者,五苓散中应重用猪苓与泽泻,轻用桂枝、茯苓,白术用量居中。 因此时病位在下焦,猪苓、泽泻归肾与膀胱二经,功专于行水,可以泻蓄于下焦之水湿,正如周岩《本草思辨录》言:“《本经》猪苓利水道,茯苓利小便,泽泻消水,《内经》三焦为水道,膀胱为水腑,肾为三焦膀胱之主。合二者观之,得非猪苓利三焦水,茯苓利膀胱水,泽泻利肾水乎?” 桂枝轻用,乃取其可以通阳化气,以助膀胱气化,诚如邹澍《本经疏证》言:“水者火之对,水不行由于火不化。是故饮入于胃,由脾肺升而降于三焦膀胱,不升者,心之火用不宣也,不降者,三焦膀胱之火用不宣也。桂枝能于阴中宣阳。故水道不利,为变非一,或当渗利,或当泄利,或当燥湿,或当决塞,惟决塞者不用桂枝,余则多藉其宣化,有汗出则病愈者,有小便利则病愈者,皆桂枝导引之功也。’’然水蓄下焦,倘若气化宣通太过,反易使水液泛滥,流于全身,不能归于正途。故桂枝轻用,宜小于全方用量的八分之一,取其轻宣之性。 若属津液不足,兼有输布障碍者,则应重用白术、茯苓,轻用泽泻、猪苓,桂枝用量居中。 脾胃乃气血、水谷津液化生之所,脾胃健则津液化生有源。白术健脾气以化水,使中焦能在大汗后津亏气耗的状况下,担负“受气取汁,变化为赤,是为血”(灵枢·决气》)的重任。茯苓此处重用,一则健脾化湿,二则其色白入肺,可使金气清降宣水之上源,还可入肾、膀胱经,以利水道。即寓《内经》所谓“饮食入胃,游溢精气,上归于脾,脾气散津,上输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之意,使脾胃化生之津液输布于全身。故重用苓术健脾输津。 轻用泽泻、猪苓,一者可化气输布水津,使之四布,而不偏渗膀胱,二者因本属津亏,重用利水药,恐有更伤津之虞。 桂枝此处用意有二:一者温阳化气助术苓输布津液,二者桂枝本身有健脾助运之功。 另在服用本方时要多饮水,以资津液之源。 若属于津液内停,脾不转输者,则宣重用桂枝、茯苓,轻用泽泻、猪苓,白术用量居中。 此时病位在中焦脾胃,脾主运化水湿,主升津液,脾脏自虚或湿邪困脾,脾之运化升清功能失职,则水湿内聚津液不布。 重用茯苓,健脾利水,加大桂枝用量,主要取其健运脾胃的作用。 至于桂枝在本方中健脾的作用,历代医家鲜有论述,其实仲景在《伤寒论》中常以桂枝作为推动脾胃运化之力的主药。如论中的小建中汤、桂枝加芍药汤等。 泽泻、猪苓轻用,亦取其免于渗利太过,使水津可以布于周身也。 总之,本方是一首调节津液代谢的方子,郭子光老先也认为:“凡是津液运行失调引起的疾病,不管其疾病在什么部位,均可用五苓散加减取效。本方实际上是调节人体津液循行的方剂。” 五苓散不仅能使津液下行而利小便,还能使津液上升而止渴,津液外输以发汗润肤,兼能通过其行津作用以祛湿化饮。凡是津液输布不利的病证,均可用本方加减。 典型病例小便不利案韦某,男,68岁。患者有慢性前列腺炎史4年。病症时好时坏,近日因外出感寒急性发作,前来门诊就诊。 症见:小便不利,频而量少,甚则点滴而下,少腹憋胀不舒,有时牵引腰背作痛,口干欲饮,伴咳嗽,汗多,神疲倦怠,心烦,眠差,大便略稀,舌质红,舌苔白腻苔,中、根部厚腻微黄,脉浮紧,关下大。 此为膀胱气化不利,水蓄下焦之蓄水证。治宜行气利水祛湿。药用五苓散加味。 处方:猪苓20g,茯苓20g,泽泻15g,白术12g,桂枝10g,车前子(布包)20g,杏仁10g,炙枇杷叶10g,牡蛎20g。 上方3剂,水煎服。 二诊:患者继服上药3剂后,小便通利,少腹不适症状消除。 按:患者既往有慢性前列腺炎史,膀胱气化功能本弱,外出感寒,表邪不解,内传于腑,膀胱气化更加受阻,不能化气成水,水蓄下焦,故小便不利,少腹胀满;津不上承,故见口干欲饮水;太阳经与督脉相连,太阳经脉不利影响督脉,故腰背作痛;表邪不解,肺气失宣,则咳嗽汗出;苔中、根部厚腻微黄,关下脉大,均提示水湿停于下焦。此属膀胱蓄水证无疑。 方用五苓散通阳利水,重用猪苓、泽泻、茯苓利水渗湿;另增车前子加大祛湿利小便之力;桂枝轻用,借其宣通之气,气化水出,兼解表邪;杏仁、枇杷叶宣肺降气,合五苓散可使下窍利。上源自洁,肺气自降,起到“水自长流不用疏”功。 用方心法泻泄案熊某,男,35岁。初诊:患者4年前由石家庄来成都工作,不久即出现大便稀溏,每便前腹部隐痛,便后痛减,食牛奶及油腻后,或情绪紧张时,症状加重,甚则大便呈水样。自服健脾丸后有所好转,但须臾又发,时好时坏。1年前做结肠镜检查示:结肠黏膜充血水肿。西医诊断为肠易激综合症。 刻诊:形体微胖,大便仍稀溏不成形,2-3次/天,小便略频,鼻头光亮,伴眠差易醒,腹部怕冷,纳尚可,舌质淡,苔白腻,边有齿痕,脉濡,关下大,左脉大于右脉,尺弱。 此为脾虚湿胜,土虚木乘。治宜健脾利湿,扶土抑木。方以五苓散加减。 方药:桂枝20g,茯苓15g,白术10g,炒香附10g,猪苓9g,泽泻9g,白芍10g,干姜10g,生麦芽20g,炙甘草6g,败酱草20g。 上方4剂,1剂/天,水煎2次。早、中、晚次分服。 二诊:服上方后,大便已基本成形,2次/天,睡眠也有好转,腹部仍觉怕冷,小便频数有所缓解,舌质淡,苔白略滑,脉濡细,关略大,齐按大于单按。 上方去泽泻,生白术易为炒白术2g,加淫羊藿10g。续服5剂。 三诊:服5剂后,患者大便基本转为正常成形,1次/天,小便频数消失,唯腹部怕冷缓解不明显,舌质淡,苔薄白腻,脉濡缓。以二诊方减猪苓,加糯米草、高良姜、益智仁,继服5剂。 四诊:患者已无明显不适,舌质淡,脉缓。以三诊方为基础,蜜炙为丸,嘱患者服丸1月。随访1年,未诉复发。 按:患者素体肥胖,胖人多湿,又来成都湿重之地生活,外湿引动内湿,困阻于脾。脾为湿土,喜燥而恶湿,湿邪困脾,运化水湿之力受阻,致水停中焦,脾不升清,湿注大肠,故而大便经常作泻;久则脾虚木乘,肝木相对偏亢,故而紧张时病甚;肝旺心神受扰,故见眠差易醒。 五苓散中重用桂枝、白术健脾助运;茯苓、泽泻、猪苓引水津四布;炒香附、生麦芽、白芍、炙甘草疏肝理脾。另考虑患者病程较久,且湿胜伤阳,故在二、三诊湿邪已去大半时,去泽泻,免过利伤阳,加淫羊藿、益智仁、高良姜等温补脾肾,以振奋脾胃之阳气。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gaoliangjianga.com/gljcd/10016.html
- 上一篇文章: 一个大补气血的方子,补气第一加补血第一,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